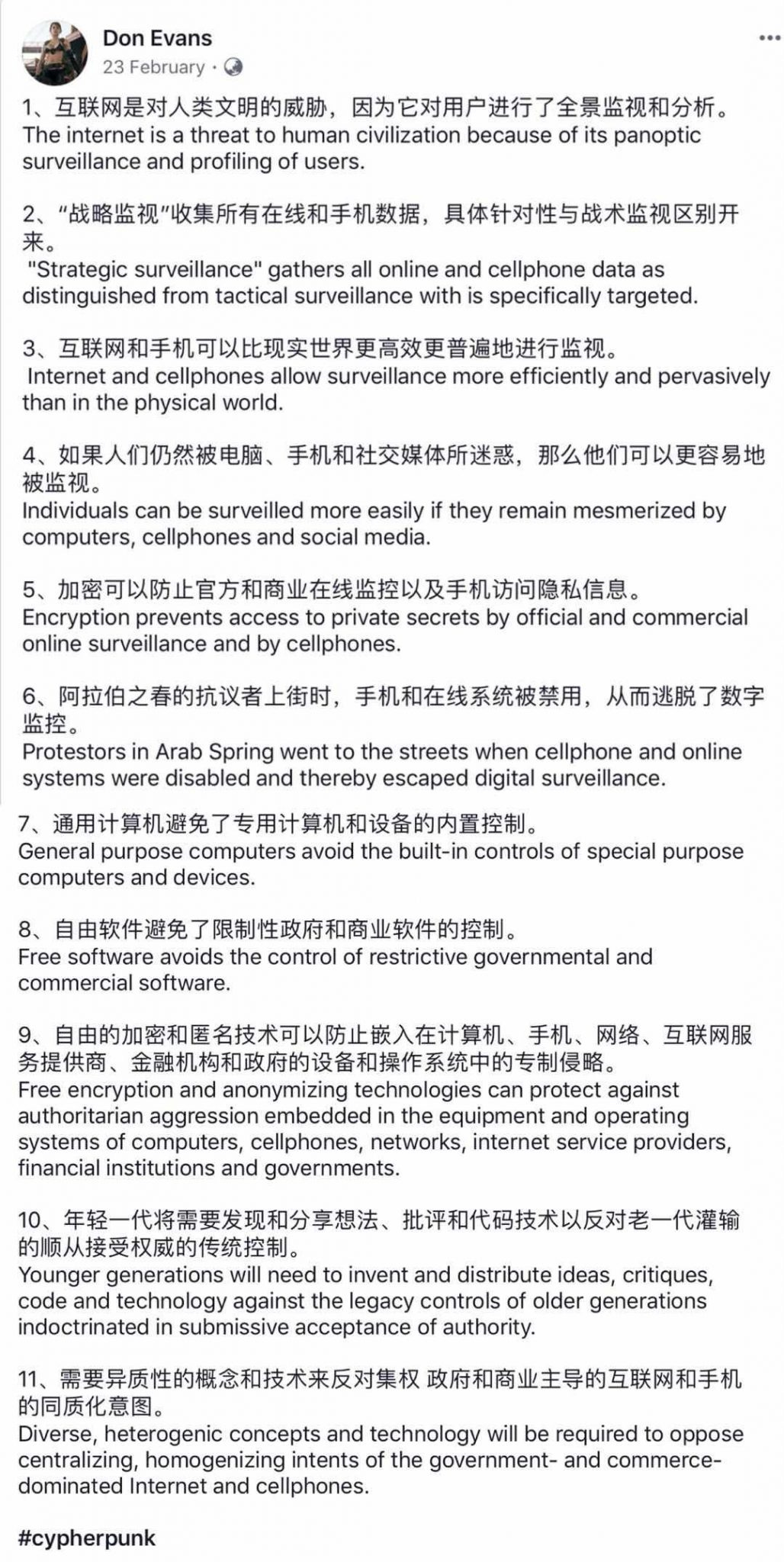互联网究竟是什么? — — 来自“监视谷”惊人的启示
【2018年7月18日存档】预先提示:如果您觉得前面的章节读起来不舒服,请从后半部分的编者按读起。但我们坚持将这些章节放在前面,以此承诺,是时候改变了
很多人曾经认真地相信“don’t be evil”。虽然这三个词经常被用来代表一种风格,但它们的主要功能只是作为一个蒸汽通风口 — 提供一种有用的渠道,让整栋建筑物所承受的压力在濒临爆炸的时候得以释放出一部分,保命。
虽然“don’t be evil”被认为是谷歌对外展示的标志性形象,但硅谷巨头们基本都有属于自己的类似的宣传形象:苹果的“与众不同”;Facebook 的“连接世界”;亚马逊盒子上的笑脸儿等等。当一个揭露出现,开始困扰这个精心构造的外观形象时 — — 当事实证明谷歌参与建造军用无人机的制造时,当事实证明亚马逊正在为警察部门制作面部识别软件时 — — 人们会感到震惊和愤怒。这家公司怎么可能这样做?!?
这些揭露挑战的不仅仅是围绕特定科技公司的神话,而是围绕整个科技行业本身的神话。毕竟,很多人都抱着这样的信念,相信这些公司正在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当人们不得不考虑揭示这些公司如何构建高科技反乌托邦的真相时,自然会大吃一惊。几十年来,科幻小说一直在警告我们的事,如今已经发生。
在这个领域,有些人似乎渴望让一个新的神话扎根:大型科技公司与军事工业联合体之间令人不安的联系是一种“新事物”。但 Yasha Levine 在其最重要的新书“监视谷”(Surveillance Valley)中巧妙地证明了大型科技公司的历史,与压制性国家机器的历史完全交织在一起。
在这里下载这本书的电子版:https://t.me/iyouport/6555
虽然许多人可能至少在名义上意识到了早期计算机、原始互联网和军队之间的联系,但 Levine 的书揭示了这些联系的深度,以及它们如何持续地存在。正如他被认为是挑衅性的说法那样,“互联网曾经是一种武器,现在仍然是武器”。
因此,谷歌建造军用无人机、Facebook 偷窥我们所有人、以及亚马逊为警察部门制作面部识别软件等等令人反胃和惊愕的状况,无需被理解为不正常。相反,这就是他们的基本生意。混蛋就是他们的真面目。
Levine 开始了他对越南战争的描述,以及被称为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的国防部的一部分 — — 该部门的出现源于相信美国能打一场必胜的高科技战争。ARPA 的技术专家们认真地相信“科学和技术的力量以解决世界的问题”,他们相信他们开发和部署的高科技系统(如 Project Igloo White )将能使美国在越南取得胜利。
虽然美国在这场冲突中最终没有取得胜利,但 ARPA 技术官僚们的世界观,以及新生科技部门和军方之间的联系,胜利了。事实上,越南制定的策略和技术很快就会用于处理国内问题,“为加强种族主义和结构性贫困的公共政策提供一个现代科学的虚伪装饰”。
Levine 的文件中关于计算机早期历史的大部分内容都植根于二战期间为满足军事和情报需求而开发的系统 — 但冷战为进一步军事依赖日益复杂的计算系统提供了充足的动力。随着人们对核战争的担忧,计算机系统(如 SAGE)的开发便出现了,以监视国家、并为军事官员提供稳定的信息流。
随着计算技术的进步,控制论思维的分散随之而来,它将人类视为信息处理机器,与计算机不同,并有助于推进世界观,其中,如果有足够多的数据,计算机可以理解世界。所需要的只是将更多、更多的信息提供给计算机 — — 事实证明,情报机构是最早利用这些系统的群体之一。
虽然这些控制和监视系统的发展伴随着向商业公司推销商用计算机的尝试,但 Levine 的观点是,这不是一种或两种情况,而是“并且/也,”计算机技术总是“双重用途”的,用于商业和军事“ — 这种分裂使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在道德上受到工作中存在的“军事应用”属性的困扰,这些人希望自己能严格地在商业或科学方面工作。
ARPANET 是著名的互联网先驱,旨在连接各个知名大学的计算机中心。依赖于接口消息处理器(IMP),系统通过各种节点在网络上传送消息,并且在一个节点发生故障的情况下,系统将通过其他节点重新路由消息 — 这个传递信息的系统可以抵御核战争的攻击。
虽然各种各样的乌托邦式神话围绕着早期的互联网,渲染它的先行者,但 Levine 强调,“监视从一开始就被嵌入其中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遗忘的 “CONUS Inter” 计划收集了数百万美国人的信息。通过将这些信息编码在 IBM 打孔卡上,然后将其输入计算机,执法小组和军队不仅可以获取有关犯罪活动的信息,还可以监视并阻止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任何社会活动。
延伸阅读:《“六行字足够绞死你”,这不是玩笑 — — 监视之恶(五)数据指控》《美国情报部门如何通过互联网大规模监视压制社会异议》
随着关于那些数据库的新闻传播到公众面前,人们产生了对高科技监视社会的恐惧,也引导一些参议员,如 Sam Ervin,强烈反对该计划。并且预示了即将发生的事态,“军队承诺会销毁监视文件,但参议院无法获得有关文件完全被清除的明确证据”。
虽然人们担心 ARPANET 的监控潜力,但这种潜力的增长却几乎没有得到检查,更多的政府机构开始建立自己的子网(PRNET,SATNET)。然而,由于他们依赖于不同的协议,这些网络无法相互连接,直到 TCP / IP 出现 — — “为今天的互联网提供支持的基本网络语言”,那些政权成功了。
然而,对公民的监视、以及公众对计算机控制的反击,并不是大多数人在互联网上熟悉的重要故事。相反,被讲述出来的故事是军事技术关于 20 世纪 60 年代反主流文化的一个非常有选择性的被过滤了的结果,以允许它以一些叛逆的可信度出现。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他将新兴的互联网从军事技术转变成了适合所有人的技术,“恰好由五角大楼经营”。
Brand 在重塑计算机和从事计算机工作的人员方面发挥了突出的公共作用 — — 将这些冰冷的机器转变为乌托邦的大门,并将计算机程序员和企业家描绘成反主流文化的真正英雄。
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机器的军事性本质在五颜六色的外套背后消失了,监视社会的恐惧被完全自由的时髦的承诺所取代。
随着 ARPANET 慢慢变成了我们称为互联网的私有化商业系统,政府与网络的联系被进一步隐藏起来。
延伸阅读:《卧室里的坦克 — — 被军事化的互联网人,以及可以怎么办》
互联网只是被称为“no real public debate, no discussion, no dissension, and no oversight“,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值得记住的是,这不是我们所知道的互联网。相反,我们所知道的互联网神话是如何构建的?正如“连线”杂志所展示的那样,“毫无疑问,无论如何使用,市场和分散式计算机技术的最佳优点和正确性都是毫无疑问的”。
从 ARPANET 到早期互联网到今天互联网的转变呈现出一个稳步发展的故事,其结果是,今天,“互联网就像一个巨大的、看不见的二进制大对象,吞没了现代世界”。就这种“吞噬”而言,很难不想到少数几家大型科技公司(亚马逊,Facebook,苹果,eBay,谷歌)他们要负其中大部分责任。在当前的互联网氛围中,人们已经很大程度上习惯了几乎陈词滥调的流行语:“如果你不付钱,你就是产品”,但这恰恰代表了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互联网是一个大型监控机器的方式。
当然,向巨人提供信息是“有道理的”,许多人(至少在早期)似乎是真的被谷歌的“不做恶”形象所蒙骗了,他们认为自己是这个神话的受益者“Google 越了解某人,其搜索结果就会越好”。像谷歌这样的公司似乎已经被广为理解的关键醒悟是,可以根据人们在网上做的事情(特别是人他们认为没有人在偷窥时所做的事情)谷歌可以了解很多 — — 人们在搜索什么,人们访问什么网站,购买了什么……
最重要的是,这些公司明白,“人们在网上做的一切都留下了数据的痕迹”,控制数据就是掌握权力。这些公司“零距离地了解我们,甚至了解那些我们对最亲近的人都会隐瞒的事”。
ARPANET 发现自己卷入了一个重大丑闻,当时它被揭露是如何被用来收集信息以监视普通人生活的 — — 而且很可能“在很多方面”实施这种监视,“然而,从 ARPANET 时代过度过来的互联网,并没有太大变化。它只是变得更强大了:蔓延了整个世界“。
但即使人们逐渐接受了互联网就是一个大型监视机器的事实,至少是行动层面的接受如果不一定是信念的话,定期发生的事件仍然会刺激这种自满。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Edward Snowden 对国家安全局(NSA)的揭露,它在全世界的报纸头版上扩大了互联网辅助监控这一事实的认知规模。
Snowden 泄露的文件揭示了“国家安全局将硅谷的全球性平台变成了事实上的情报收集机构”,这些文件暴露了“硅谷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共生关系”。
然而,在随后的骚乱中,硅谷却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将自己描绘成受害者。 Levine 将其中的一部分归功于 Snowden 自己的自由主义政治倾向,他成为了技术爱好者、密码朋克和被互联网倡导者崇拜的英雄,“他曝光了硅谷在互联网监控中被隐秘已久的角色”,同时推进了自由主义者对“计算机网络乌托邦承诺”的信仰,类似于 Steward Brand 所宣称的那样。
在许多方面,Snowden 作为早期技术自由主义者的完美继承人出现,特别是因为他(像他们一样)更少关注大规模的政治行动,而更多地关注通过技术获得救赎的思路。而 Snowden 的首选技术是 Tor。
虽然 Tor 可能将自己作为了避免监控的解决方案,并被许多最坚定的拥护者支持,但 Levine 对此表示怀疑。注意到“ Tor 只有在人们致力于维护严格的匿名互联网例程时才有效”,Levine 认为 Tor 提供的是“虚假的隐私感”。Levine 描述了 Tor 的起源,最初需要为政府工作人员提供在线匿名访问互联网的能力,而不会泄露他们的真实身份;并且为了使 Tor 有效,该平台需要扩展其用户群:“Tor 就像一个公共广场,群体在那里组建的规模越大,越多元化,间谍们就可以更好地隐藏在人群中”。
延伸阅读:Tor 从来没有否认这点《当搬石头砸脚遇到“运动死亡”》
虽然 Tor 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非盈利组织剥离出来了,但它仍然依赖于美国政府的大部分资金,Tor 旨在通过强调其激进主义用户群以及与 Wikileaks 等新闻组织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来解决这个问题 — — 标示自己摆脱美国政府额立场,因为那些群体经常与美国政府发生冲突。
在斯诺登的形象中,Tor 找到了一位完美的公共倡导者,Snowden 似乎是 Tor 价值的活生生的证据 — 毕竟,他成功地使用了 Tor。然而,正如 Ross Ulbricht(丝绸之路的“Dread Pirate Roberts”)所证明的那样,Tor 可能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完全安全 —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找到了一种廉价而简单的方法来破解 Tor 的超级安全网络“。(我们还没有看到过这一研究的具体报告)
更糟糕的是,Tor 已经被国家安全局当作了蜜罐,被认为是“有人在那里做坏事”的线索,令使用者遭受更强针对性的监视。
对于加密消息服务 Signal 来说,有着大部分相同的故事 — 它是由政府资助的,并且不像其粉丝所认为的那样绝对安全(互联网本来就没有绝对安全)。当然这些工具对于致力于保持匿名的高技术文化人员来说是很有用的,但“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这些工具提供了错误的安全感并提供了与隐私相反的功能”。(请注意,这里他指的是,美国政府可以做到全面监视,打破上述加密技术,几乎没有第二个政府可以做到这点,因为美国有霸占互联网的地利)
互联网的中心神话将其视为由乐观嬉皮士建立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希望通过高科技工具拯救世界免受侵入性政府的迫害。然而,正如《Surveillance Valley》所述,“计算机技术无法与其开发和使用的文化分离” — — 监控一开始就是互联网的核心,也一直都是互联网的核心 — 这里有着政府机构和巨头公司无处不在的眼睛。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无法通过技术方案来解决。
支撑互联网的自由主义精神适用于科技巨头和密码朋克,但真正的替代方案并不是一套工具,允许有技术能力的极少数人能够保护自己的隐私。
终极解决方案是真正的互联网民主化。
注:我们删除了一部分内容,大致原因在于文章太长了某些平台不支持这一长度。被删除的部分或许是最具争议的部分,说实话,我们是在高强度的批判性思维基础上尽可能保持冷静阅读的。为什么会这样?详见如下的分析。
编者按 — — 如果上述章节让您感到不舒服,我一点不会觉得奇怪。我几乎被击碎了,醍醐灌顶的冲击,它说出了我一直深感困惑却无力说出口的东西。因为要想承认这点,首先就要粉碎那些曾经支撑我们所有人希望,我们几乎全部力量的源泉。这太残酷了。
但自己骗自己肯定不是解决方案。无休止的监控和反监控、入侵和反入侵、封锁和反封锁的战役,看不到尽头的消耗,而数字极权一直走在前面。我们能坚持在这场战役中的力量来自我们告诉自己要相信水涨船高,相信猫鼠游戏是我们所有人的宿命。但它不是,恰恰是那些我们一直专注的东西,似乎错了。
是时候反思这个问题。在我们被耗尽之前。
这本书是对互联网的起源和当前状态的一系列史上最毫不留情的观点。Yasha Levine 可以说是以惨无人道的方式将所有人的视野撕开了,他强调发展到今天的这个互联网本来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监视工具,而不是人们能理解到“谷歌是坏蛋”就够了。
虽然 Levine 陈述的大部分历史对技术历史学家或那些精通技术批评的人来说并不陌生,但《Surveillance Valley》这本书中将许多(通常是单独的)线索带入同一个叙事中。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早期历史常常被放在一个孤岛中,而科技巨头的崛起则被放在另一个孤岛中,而 Levine 将它们组合在一起了,以至于足以展示连续性并让它们能够得到更为充分的理解。
Levine 的描述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了早期社会对 ARPANET 的反击(互联网的前身),那是一系列经常被遗忘的事件,完全值得推出一本自己的书。
Levine 还描述了 20 世纪 60 年代的学生们,他们在早期的 ARPANET 项目中看到的是“由全国各地大学校园的勤奋研究人员和工程师们悄悄组建起的网络化监视系统,政治控制系统和军事征服系统。
同样,Levine 强调了 NBC 从 1975 年就开始报道了的 CIA 和 NSA 通过利用 ARPANET 项目对美国人进行的间谍活动 — — 比斯诺登早三十年,以及参议员为抵制这一项目所做的努力。尽管 Levine 没有提出也没有声称要提出一个有关阻碍和抵抗的综合历史,但他的说法清楚地表明,关于技术解放的主张经常遭到怀疑,而大部分怀疑论被证明是具有高度先见之明的。
这是最令人焦虑的部分,一个关于如今“我们正在做什么”的痛苦自省。
然而,那种抵抗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遗忘了。随着被渲染成技术力量的所谓“twitter 革命”占据各大报纸的头版,新媒体“转型”和互联网创业被夸夸其谈,几乎没人再愿意提起这一文化肮脏的起源,美丽的神话被编织得栩栩如生,一切都被扭曲了。
这种扭曲将互联网的起源,在公众的想象中,从越南的反叛乱武器转移到了加利福尼亚的反主流文化社运。这是彻头彻尾的变质。以至于当十几年前,数字极权的概念被抛出时人们的表情是惊讶的,甚至认为它只是学界象牙塔里的矫情;当几年前监视资本主义的概念被叫响时,人们的表情是困惑的,就如同看着 #deleteFacebook 运动后几乎纹丝未动的广告利润额……于是,具有“最大”视野格局的人开始思考,“我们是否应该扔掉这个 internet?”
无人回应。因为所有人都明白,这几乎不再可能。我们打造了一个牢狱,把一切都装了进去。就如我曾经在《百忧解时代》系列文章中介绍过的一部让人揪心的流行小说所描述的那样:
“我从未想过要让这一切发生,它运作的太快了。我从没构想过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圆圈中的所有成员都被迫执行命令,所有的统治、所有的生活组成同一个网络……曾经我们还可以选择退出,但现在不行了,“完成”已经是最后阶段,我们把所有人都锁在了圆圈里。每一个人都对其他人保持着完美透明的圆圈,绝对力量和绝对无能的圆圈。这是极权主义的噩梦……”
这段话来自 Dave Eggers 在2013年写的一篇名为《圆圈》的小说,讽刺数字世界的圆形监狱本质。有些人认为这部小说不过是《1984》的模仿版,但 Dave Eggers 在结尾部位也就是上面这段文字中,上升到了奥威尔没有达到的层次 — — 它展现出一种处于“完成”阶段的极权主义噩梦的超人类力量。
这大概是第一部针对性揭示这个互联网本性的艺术作品。从这一角度上看,《Surveillance Valley》的观点已经不算出奇。但它最出奇的地方在于,对于解决方案的极端性表述。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样,他认为我们所有人的努力,曾经那些无休止的消耗,一钱不值。
因为我们被困住了,被困在了那个“圆圈”里。我们所有的挣扎都建立在这个圆圈仍然完整的基础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赢不了。
在此有必要说句公道话,在某些部分 Levine 遭到了严重的误解,比如这本书中关于 Tor 和 Signal 等加密工具的章节,绝对是最具争议的,因为他的论述让自己彻底摆脱了技术本身,而我们所有人都在技术层面上思考,一直以来,或者不客气地说,是在自卫的层面上思考。被动挣扎。这正是 Levine 所反对的,他提出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如此被动?
也要怪 Levine 嘴臭,太不留情面,至少不够尊重他人的工作。但是如果你在阅读《Surveillance Valley》这本书之前就熟悉 Levine 所报道的新闻的话,你将会知道,他的大部分报道都涉及加密技术,如 Tor,以及类似的隐私保护技术。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Surveillance Valley》完全可以被视为那些报道的产物。只是视角升级了。
所以必须指出:将 Levine 的书定义为“攻击 Tor(或项目工作者)“是完全错误的,彻头彻尾的误解。
Levine 对 Tor 的评论与他的书中更大的论点的主旨相一致:这种隐私工具是高科技社会创造的问题的高科技解决方案,主要用于让人们沉浸在所有这些高科技系统中。
他质疑 Tor 的政治,并指出“硅谷担心政治解决隐私问题,而 Internet Freedom 和加密提供了一个可令硅谷接受的解决方案“。于是这一方案无法撼动囚困我们的“圆圈”,它只是令当权者困惑,而我们的对手不仅仅有现实中的当权者。
或者,换句话说,Tor 有点像在 Whole Foods 购物 — — 关心食物的人愿意花更多的钱来获取他们的食物,但最后购物本身让人们感觉良好,人们并没有真正挑战更广泛的体系。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Levine 对 Tor 的批评中最主要的因素并不是说 Tor 的匿名能力不行,对某些人(如斯诺登)来说,Tor 显然是非常高效的隐私保护手段,但是对于大多数不知道该如何正确使用它的用户来说(并且不愿意真正完全地使用加密作为生活方式的人),它就完全保护不了这些人。
我们一直意识到这个问题。目前这种模式的互联网自卫运动的结果很可能是让少数技术精英获得了隐私特权,然而对于大多数不懂技术的人来说,很多匿名工具难以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很多人根本无心学习那些技术。而作为基本人权,隐私权应该是人人享有的,正如匿名者组织的口号:只要有一个人尚未自由,我们所有人都不会自由。
于是我们就事论事地寄希望于技术推广、更便捷的加密方法来保护更多的人,直到它能保护所有人,将监视资本主义隔离在外。我们为这个幻想拼搏了多年,直到被 Levine 这本书惊醒。他说的没错,即便这个幻想成真,我们依旧没能打败数字极权。
我们认为他是对的。这一中心观点与《Surveillance Valley》全书的一个微妙主题保持一致:用技术代替政治。因此,在他的书中,Levine 不仅将互联网视为权力剥夺的根据 — — 因为它依靠监视并依赖于大型企业而存在,并且他强调,互联网的意识形态核心如何将所有政治行动集中在了技术上。对于每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互联网都将其作为解决方案 — 但 Levine 不愿意接受这一想法。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Levine 在一定程度上误会了密码朋克。他似乎认为密码朋克是原地自卫,也就相当于没能真正认清互联网的本性。完全不是这样。密码朋克几乎是最早提醒监视资本主义的人,在媒体鼓吹“Facebook 革命”期间不断地警告这一危险性(见下图),并且也是去中心网络重塑长期坚定的支持者,与 Levine 的结论并不矛盾。以下是密码朋克的概述。
如果 Levine 认为密码朋克会反对这本书中的观点,那就错了。至少我,密码朋克老牌支持者,完全认为无需辩论,我们与 Levine 的目标是一致的。
并且,尤其重要的是,要解决监视世界的问题需要极为复杂的工作和也许较为漫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在数字极权掌下的我们所有人能做的最有效工作就是加密,为了保证工作能继续进行,我们必需能做到首先让自己从这个监视网络中脱离出来,而密码朋克的工作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所付出的努力。
延伸阅读:《如何才能挑战 Facebook 并取得胜利? — — Distributed Social Network》
Levine 之所以被认为是最大的异端,恐怕是因为他拒绝向 Stewart Brand 和 Kevin Kelly 等早期的大牌技术爱好者致敬。
并且 Levine 还撕毁了我们很多人心目中的英雄,他批评了一些团体和个人如何在“仍然是 ARPANET”的情况下警告互联网,是的这其中包括我,但他也更加强调了这些人最有可能有助于创造更好的替代方案和曾经未被采取的路径,他们是互联网革命的希望。
在这本书的结尾部分 Levine 指出,“我们生活在萧条时期,互联网是他们的影子:由间谍和强大的公司经营,就像我们的社会完全由他们经营着一样。但这并非完全是绝望的“。
是的,并非完全绝望。尽管 Levine 提出了民主行动作为必要的回应是值得尊敬的,但这是一项冗长的工作结束时才能有的解决方案,就如我们一直在做的那样,Levine 也强调了互联网如何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民主。所以,
这本书指出,仅仅谈论民主是不够的,人们需要认识到某些技术是民主的,而其他技术则不是。尽管我们不愿意承认,但也许互联网根本就不是民主技术。当然,我们也许可以将它们用于民主目的,但这并不能使技术本身变得民主。
结尾,可以再强调一句:《Surveillance Valley》这本书对结交很多朋友并不是特别感兴趣 — — 它不可能获得广泛认同,它也不做这种期待。一方面,它消除了关于互联网的令人欣慰的神话 — — 这些神话曾经在很长时间里是绝大多数人能坚持到今天的唯一支撑(包括我),另一方面,它推翻了经常被吹捧为解决许多互联网问题的工具 — — 一种毫不留情的,毫无情面的,可以说是极为残酷地打击(包括对我)。
我们承认,《Surveillance Valley》是一本非常令人不安的书,但它是一本重要的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需翻译它。它打破了令人欣慰的神话,并拒绝给读者留下简单的解决方案。最为印象深刻的是,它指出,军事 — 工业综合体的全球性大规模监视和各种惊人的侵犯性事件,并不是互联网“出现问题”的迹象,而是,这个互联网按照预期运作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