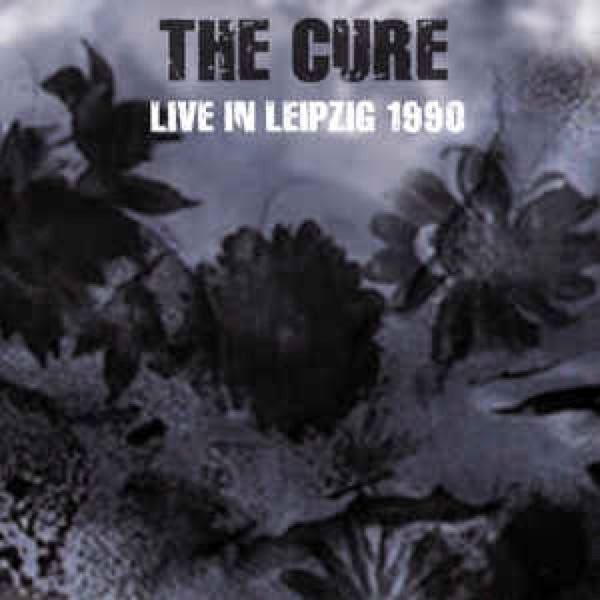柏林墙倒了吗?(2):条顿式媚俗和莱比锡翻页
【 2020年6月5日存档】从与我交谈的人那里,我一直听到这个奇怪的词语 — 他们说,过去我们活在法西斯主义之下,然后活在共产主义之下,而现在,他们说,我们是活在民主 “之下”。这不是一种怪异的谈论民主的方式吗?就好像它只不过是另一个你必须服从的体制?
如果您还没读过上篇,在这里看到《柏林墙倒了吗?(1):五味杂陈的卡巴莱》。
20世纪80年代,事情通常发生在 “学院派”;到了90年代,场所转到了U-2,这是附近一座灰色石板办公楼地下室里的迪斯科舞厅。
它的音乐来自慕尼黑,啤酒来自慕尼黑,迪斯科DJ来自慕尼黑,子弹机和干冰也是来自慕尼黑。
那个地方天花板很低,墙壁随着声音震动,节奏透过脚底传上来,你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麻木状态。
女孩子们在大喇叭上跳着独舞,甩动、摇摆、推伸、甩动、摇摆、推伸…… 她们闭着眼睛,在声音的洞穴中独自舞动。男孩子们徘徊在弹球机之间,从一个电子游戏逛到另一个,眼睛瞅着女孩子们。
世界任何地方都有这样的迪斯科舞厅,但是,这里,这个低矮的地下室曾经是秘密警察的审讯室。
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它并不是十分 “秘密” 的事。吧台后面的女孩子们会讲给你听,甚至指给你看,墙上还留有原来囚犯画的壁画。
多年来,这个组合难以抗拒:斯塔西的虐待狂魅力遇上慕尼黑迪斯科舞厅的色情狂魅力。
引入U-2 是以一笔代价打开了两个被禁闭的世界。但被禁的魅力已经完全消失,现在这里是一个迪斯科舞厅,跟其他地方没什么两样。酒吧的女孩在我耳边喊:“一切都很酷!” 节拍震颤地板,频闪灯将她干净白皙的脸庞变成了一张蝴蝶面具,舞动着,漂浮在空中。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past” does not imply a serious working through of the past, the breaking of its spell through an act of clear consciousness. It suggests, rather, wishing to turn the page and, if possible, wiping it from memory.”
在整个民主德国,斯塔西拥有50万情报人员。从前,放置在像这样的建筑物里的档案纸张有数以亿计;咖啡馆里的窃窃私语、公共汽车上的道听途说、断章取义的同事间闲聊 —— 这是一个索引细致的、收录全社会异议言论的图书馆。
告密的圈子变得如何宽泛,以至于任何人如果能重新找回公民勇气都是个奇迹。
但确实有些人做到了。而那些没有做到的人,现在,总是挥舞着手指做着令人厌倦的、自我辩护的同样手势:“那是我的世界。那是我知道的一切”。
什么能让人明白,一个审讯中心变成迪斯科舞厅的事实呢?这儿是不是应该搞个纪念馆或者博物馆取而代之?
音乐的声音如此喧闹,折磨着你已近中年的内心,充塞着内心每一个空虚的地方。
“与过去妥协”,并不意味着对过去严肃的解决,不是通过一种清晰的、有意识的行为来打破魔咒。毋宁说,它希望翻过这一页,并且,如果有可能,从记忆中彻底将其清除。 —— Theodor Adorno 《与过去妥协意味着什么?》(1959)
问问你自己,那吧台里正调制鸡尾酒的女孩,或那头发锃亮、穿着贝纳通 “世界之彩” T恤的男孩,他们是否应该了解人们曾经在这里被殴打、被审讯的事实?摆出一副庄严的脸色吗?难道与强烈地渴望忘记所有过去相比,庄严是更为真实的 “与过去妥协”?
我不能问酒吧里坐在我旁边的小夫妻这样的问题,他们的脸在频闪灯下犹如一对舞动的唱盘。
怎么期望他们了解我说的东西呢?Erich Honecker 对他们而言已经是久远的历史。在他的政权倒台时,这些男孩女孩还很小。
我会听他们说:“那不是我的问题。那不是我的过去”。
民族会战的记忆
它像一个巨大的、用烟熏成黑色的花岗岩搭成的条顿式火葬堆,切割得粗糙的石头向天空兀立,它们似乎要把某个强健武士的身躯奉献给火焰。
只是在这个纪念碑的最高处,应该放棺木的平台上,什么都没有,没有身躯要奉献给天空,只可以从这儿纵览城市的全景。城市则围绕它而发展成长。
它如此巨大,超过欧洲所有其他战争纪念物:一座怒目而视的威廉家族石堆,孑然独立,像家族里最执拗的成员站在莱比锡郊外的一个公园里。
就其恶劣的好战趣味,以及僵硬、粗野的纪念碑样式而言,它完全是一种尴尬。
雨水如丝,落在它厚重的表面,它似乎在嘲笑:来吧,试试将我焚毁,你会失败的!我太大了,我在这里太久了,我比你们都要长命……
德国从1871年统一后不久,开始纪念1813年的民族会战。当时,100万来自俄罗斯、奥地利、英国、法国、德国、和波兰的士兵激战一天,决定了欧洲的命运。
拿破仑在那一天最终战败,标志着他的帝国开始没落。那是第一次,来自德意志各公国的人们站在一起,作为德意志人而战斗,即使部分德意志人也站在拿破仑一方作战。这个战场仍被宣称为德意志民族的诞生地之一。
这个纪念碑正是为此而建的,1913年会战100周年纪念典礼上,德皇威廉二世为它的落成揭幕。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检阅台旗帜飘扬,帝国羽饰犹如丛林,胸甲闪闪发亮,紧绷的绑腿掖在长筒骑兵靴里,刀剑在腰间叮当作响。
冷酷的帝国面孔,脚跟咔嚓并拢致敬,戴头盔的人们互相轻轻点头致意 —— 这些牵线木偶们明白自己处于荣耀的顶峰,那种在他们头顶屹立的巨大石堆所象征的荣耀。
装饰纪念碑的雕塑家选择向威廉家族献媚,将他们刻画成条顿武士。在纪念碑底座的雕塑饰带上,有这样一个大师形象,是画成德意志武士的圣米迦勒(基督教大天使),头盔环绕面颊,眼睛凝望德意志早已确定的伟大未来。
环绕他周围扭动着自然世界的象征:狮子、老虎、龙,全都听从他的意志;还有一条超长的斑点蛇,嘶嘶着,微笑着。
这些动物充满了矛盾:它们是内心的魔鬼,还是邪恶的力量?似乎都有,因为他的目光既犹疑又果决,既痛苦不堪又坚定不移。
在圣米迦勒的左边,有一对挤眉弄眼的死神头颅,像斜眼的猴子一样在嘲笑他庄严的目光。
“Besides awe and fear, there was the shiver of being in the presence of the new.”
20世纪30年代有一副著名的海报,元首装扮成一个日耳曼武士,穿着闪亮的胸甲,佩剑,骑在马上,高高举起一面血红的旗帜。我一直认为希特勒和戈培尔在运用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人物和形象中,显示了某种创造力。
事实上,我还一直认为,这种艺术的创造性 —— 纳粹首席建筑师 Albert Speer 呈现在他的建筑物中,纳粹著名导演 Leni Riefenstahl 呈现在她的电影中 —— 有助于解释纳粹在人们心中激发的那种极端狂热。
除了敬畏和恐惧,还有身处全新呈现方式的战栗。
但作为政治艺术家,他们的创造比我曾经认为的要少。纳粹吸引力的全部色情用品都已经在这了,在莱比锡的那个纪念碑:同样的头盔、同样的蛇、同样的条顿式激情、同样滑稽的男性阳刚崇拜,同样对本性充满色情的迷惑。
它是创造生命的力量?还是淫荡的怨恨?全都在这儿了。希特勒不是政治艺术家,只是一个熟练的低俗品味鉴赏家。
没有不媚俗的民族主义艺术,没有不扮演真挚情感的爱国主义创造。为什么?也许一切非个人化的艺术都不可能是真正的真诚,而民族主义艺术从定义上就不可能是个人化的。
也可能,民族主义艺术不可能创新,它固着于可资利用的传统,或者,如果未能做到这一点,则固着于媚俗,在这里是条顿骑士的日耳曼黑森林。
希特勒对日耳曼历史的拿来主义,只限于利用19世纪中期一种庞杂的、狂热的伪善情绪。因此,正如德国哲学家 Adorno 提出的,原装货和抄袭货都意味着一种连自己也不能完全相信的民族主义形式。
这个纪念碑的峭拔巨大是一种怀疑的自白,希特勒的模仿也是。为了让人信服,两者都必须威吓。
这种对媚俗图腾过于夸大的模仿并没有跟着希特勒一起终结。
身着领巾和皮短裤的希特勒青年团曾手持火炬向纪念碑进军,并以向德意志帝国(Reich)致敬的仪式作为结束。
在图片中,你可以看到火炬在观赏湖面上闪闪发光,烟雾缭绕在火红的天空。
民主德国坚持它已经和法西斯及资本主义的类似过往彻底决裂。然而,自由德国青年团(Free German Youth)的领巾和短裤,叙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被称为 “青年奉献” 的青年成人礼 —— 许多声音高呼对新国家的忠诚 —— 甚至复制了旧有的瓦格纳火炬仪式,天空中火红的烟雾怪诞地映照在观赏池中。

“但你还期望其他什么呢?” Helmut Börner 说。他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做了个表明自己既绝望又生气的手势。
“这是我们的世界。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
Börner 先生是纪念碑隔壁博物馆的馆长。他会觉得民主德国复制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巾奇怪吗?他说不,他说是我搞错了:“我那个年代,在先锋队的时候,我戴的是蓝色的领巾。我父亲那个时候是黑色的领巾”。
我说:“但是,它们还是同样的领巾”。
“啊”,Börner 先生说着,从我身边溜到玻璃柜后面。那里面有法国胸甲骑兵的制服,一些大炮用的霰弹、老式的火枪和一面鼓。
“这是旧瓶装新酒。旧瓶子还很完美。我的父母没有将它们丢掉,他们只是把白酒换成了红酒”,他就此想了一会儿,“是的,也许就是这样”。
“但是,新酒不会被旧瓶子污染吗?”
他透过厚厚的镜片眯眼看着我,捻着自己红色的短须,退回到博物馆更远处的另一个玻璃柜后面。然后他问我,是否曾经离开自己的家庭,尝试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我说,没有。
“那么,如果你那样做了,你不会把旧的扔掉。你尝试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在各个方面都要比已经失败的旧生活更强”。
他指向一个玻璃柜里的一幅小水彩画。它描绘了一群莱比锡妇女在战斗结束后帮助把伤员抬上马车的情形。
“他们是法国人还是萨克森人、或是普鲁士人、瑞典人、奥地利人、或俄罗斯人,完全不重要。她们一视同仁地照看他们”,他平静地说,“当然,你不能拿今天他们能得到的那种看护来比较。他们成千上万地死亡,死于伤寒、神经和伤口感染,已经开始做截肢手术。那么可怕,我们无法想象”。
如果是在1813年度过他的余生,Börner 先生会更快乐些。那样会更简单,我会同情他。谁想要解释一个党员如何应对自己的世界的崩溃?
“我比共和国大一个月”,他用自己那种平静的、沉思的、间接的方式说着,“我生于1949年9月,所以我在这个时期,在这个国家,这个社会长大。那是我的世界”。
当局让他探查遥远过去的安全性,并认为只有他的展览强调了俄罗斯和德国军队在莱比锡铸就的历史友谊。这很容易做到,因为他们曾站在同一边战斗。
有一些苏式制服的展览把这一友谊呈现于现在,但制服占据了太多的空间,他在1988年得到许可,把它们处理掉了。
他没有任何理由假装自己不是党的一员。他依旧希望历史能 “仁慈地批判” 民主德国,它比他自己周围正在形成的社会更为 “平等”。而且民主德国生存正在和平中。民主德国没有军队参与过战斗。
(编者注:如果您曾经读过《二手时间》,或曾经与中国的毛泽东崇拜者交流过,也许您对这种情绪不会陌生)
我问,甚至在捷克斯洛伐克也没有吗?1968年?没有,没有,他坚持说,也许有后勤支持,但从未有作战部队。
他希望历史能冷静地批判民主德国。但他知道,历史不会作出裁判。根本不会有清算。要发生的已经发生,民主德国政权的每一缕踪迹都被扫进了垃圾桶。所以10年后新的一代将很少相信它曾经存在过。
我自己在想,应该有一个民主德国的纪念馆,摆满特拉比和沃特伯格汽车(前民主德国著名品牌),从建筑物的山墙上拆下来的锤子和镰刀,体育英雄的图片,埃里希昂纳克的呢帽,一些斯塔西档案,隐形麦克风,重修的审讯室,一座原始大小的度假狩猎小屋。
Börner 先生笑了。他说,博物馆永远是成功者的存档、胜利者的圣殿。
但是,应该有关于错误的博物馆,我说,尤其是对于摧毁生命的错误。问题是,他说,谁会想参观这样一个博物馆呢?
“This effacement of the DDR, Börner knows, is very German. Every fifty years, the nation’s past is rewritten, and the lives that were lived under other conditions are suddenly stripped of all their sense. ”
Börner 先生知道,这种对民主德国的抹杀,正是德国式的。每隔50年,这个民族的过去就被重新书写,那些生活在其他状态下的生命突然被剥夺了他们所有的感觉。
这伴随着 Börner 先生的父亲,纳粹时期的一个学校老师,也伴随着 Börner 先生自己。他说,只有人类如此,因为人们想要压制过去。
“在私人生活中可能也是这样,什么事情错了,让你失望了,你想将它关闭,在下面划一道线,再也不想提起它”。确实非常人类化,但人们想知道,各民族是否允许它们自身像个人那样被遗忘。
当对党员的清洗 —— 像他这样的党员 —— 波及他在博物馆角落里满是灰尘的办公室时,Börner 先生被迫辞去工作。在新形势下,他觉得自己会活得更好,像他一直以来做的那样,通过只信任 “某人最亲密圈子里的一些人,人们可以依靠这个圈子。在这里人们会感到快乐”。
东德人不停地哀叹与资本主义一同到来的生活的私有化(这些天每个人都在为他们的前门买锁)。事实是,它只会增强在社会主义之下已经存在的生活的私有化。
Börner 先生也知道,相比发生在他父亲身上的遭遇,在他身上将要发生的事儿会温和得多。
1945年,成千上万的纳粹分子受到苏联战时军事法庭的审判和枪毙。他自己的父亲在一个苏联集中营中待了四年,认为自己足够幸运,得以活命。1989年革命以来,对过去的清洗没有牺牲一条性命。这很了不起,Börner 先生说,我们德国人并不总是重复错误的。
令他最困惑的是,为什么他曾让自己相信,为自己考虑的风险远远超过实际的风险?这是他最为后悔的。
“我当然可以更勇敢些,因为我们当然会害怕,会有恐惧,今天的结果证明这种恐惧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给自己施加某种形式的自我审查,那是不必要的”。
当他谈到这里时,映照在玻璃展柜上的脸庞突然显得悲痛和困惑,仿佛他无意中发现了当局将他轻易握于股掌的秘密。太晚了。
他带我走出博物馆,我们站在斜对面民族会战纪念碑的阴影下面。我问他,纪念碑是否并不代表某种德意志理念?
他笑了,“在民主德国,我们不谈论德意志。” 德意志是被禁止的话题。身份认同是与国家、与社会主义、与对伟大苏维埃母国的友爱联系在一起的;但与 Deutschland、人民、世代相传的记忆,没有关系。这些是反动资本主义的谎言,以沉思的条顿人的圣米迦勒为代表。
然后,Börner 先生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他说:“我很高兴民主德国没有建造自己的民族会战纪念物,从未尝试用石头建立它的德意志理念”。
“为什么没有呢?”
“你能想象,如果有,它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他说,突然进入一种自由思想的明亮光芒中,“它应当是一个混净土地堡”。他再次哈哈大笑,“是的,一个混凝土地堡,那是民主德国留在身后的一切”。
生活于民主 “之下”?
“There seemed only one thing to do: blow it all up and start over again. And that included the workers. They would have to relearn all the German virtues: good timekeeping, cleanliness, application, hard work. Moral of the story? States make nations; socialism deforms national character; regimes can ruin a people, even the Germans.”
过去,东德人在社会主义体制中的生活状况相对较好,给西德人提供了一个德意志自恋的机会。东德是最为成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这个事实似乎证明,德意志的美德甚至胜过计划经济之类的布尔什维克理论。
换句话说,民族强于国家。
墙倒下了,西德的实业家们来了。他们参观东德的工厂,仔细查看机器,盘点工厂、建筑物、原材料,记录工人每小时的生产率,等等。
然后他们回到斯图加特、法兰克福和慕尼黑总部,面带焦虑。东部是一片灾区。
似乎只有一件事可以做:推倒一切,从头开始。其中也包括工人 —— 他们必须重新学习所有德国人的品质:守时、干净、实干、努力。
这个故事的道德意义是什么?国家制造民族;体制可以摧毁一个民族,即使是德国人。
Karla Schindler 褐色的头发剪得很短,像男子一样的短发,露出时髦的环形耳环。50岁出头的她还记得自己进入莱比锡棉纺织厂的那天。
那是1953年9月1日。她的母亲在她之前进厂,她的女儿在她之后进厂。40年的工作,她能展示的是两张证书 —— 社会主义管理部门的致谢,证书装饰有民主德国的锤子和镰刀标志,以及最冷冰冰的东西 —— 科学量角器。
她还有持续多年的咳嗽顽疾,这是40年来在棉花机器上工作的结果:在棉丝的阴霾中呼吸,阴霾如此浓密,有时她甚至看不到相邻的工人。
她应该痛恨这个巨大的、摇摇欲坠的19世纪大杂院,这儿挤满了厂房和工棚,然而她围着它忙碌;跟叉车上的男人聊天,与守夜人开玩笑,跟机房的女孩子分享秘密。
“我为什么要恨这里?这曾是我的生活。现在还是”。Schindler 夫人是工厂在特洛伊汉德的代表,这个组织正在将东德的工业部门私有化或者关闭。
西德人想关闭工厂。Schindler 夫人正奋力抢救它。
“有一位犹太绅士,他的家族从前拥有这个工厂,他对它有兴趣”。
她满怀希望地说着,带我进入第一车间。那是一个旧的工业地狱,里面所有的东西 —— 墙壁、宝石蓝机器、塞满了棉花包的笼子,都覆盖着白色棉花丝。
空气中是黑褐色的棉丝和灰尘悬浮物,映照在污迹斑斑的窗户中透过来的微弱光线之下。一个老人正在把原棉送入一个分离器,它将原棉拉扯成丝。
Schindler 夫人把手伸进一个棉花包中:“从乌兹别克斯坦来的。苏联,没救了”。
那就是工厂存在的秘密:从苏联帝国的亚洲地区送来廉价、低质量的棉花,勤劳的德国人将其变成廉价的棉纱,供应给克拉科夫、布达佩斯、或莱比锡的贫穷家庭主妇。
这无法继续下去。Schindler 夫人知道这一点。没有优质的原材料和新的机器,这个老家伙将在几个月内失业。
“We used to live under fascism, they say, then we lived under Communism, and now, they say, we live “under” democracy. Isn’t that an odd way to talk about democracy, as if it were just another regime you had to submit to?”
莱比锡纺纱厂是一座对某种劳工乌托邦、某种归属和同志友谊的纪念碑,不管社会主义有多少其他的错误,对于 Schindler 夫人这样的人们,这是真真切切的。她从未完全相信它的一切。
这儿曾有一种军事体制,要求各个队伍互相竞争,以完成生产指标。在通往纱纺车间的门口,我们看到一个陈旧的牌子,上面写着 “民族队伍之间的友谊”。
当然,意思是俄罗斯和德意志民族之间的永恒的社会主义友谊。“这个怎么样?” 我问她,她扬了下眉毛,似乎说,你在开玩笑吗?
纺纱车间里面,有两三个穿浅色透光连衣裙的女孩子,透出下面白色的内衣。她们在皮带上来回拍打,将已经满了的纱锭扔进齐腰高的红色箱子里,把新的纱锭装上去。
Schindler 夫人凑上去听她们抱怨一种新的亚麻线给她们带来的麻烦。她不必告诉她们,她们的工厂就如她们用牙齿咬断的线一样脆弱。
这个古老工厂的一间间厂房、一层层楼,现在都关闭了,机器盖上了塑料布,地板上灰尘堆积。
在楼上的办公室里,有散乱的盆栽植物、描绘保加利亚海滨游客欢乐的褪色海报。她告诉我,特洛伊汉德将她置于两难抉择的境地。他们会告诉她拯救这个工厂,作为交换,她必须解雇绝大多数员工。
不过,她坚持认为,情况正在改善。她可以挣德国马克,可以去西德旅行。“那里很迷人”,她充满渴望地说,仿佛是在谈论塔希提的岛屿,“那里的空气多么清新”。
我告诉她,从与我交谈的人那里,我一直听到这个奇怪的词语 —— 他们说,过去我们活在法西斯主义之下,然后活在共产主义之下,而现在,他们说,我们是活在民主 “之下”。
这不是一种怪异的谈论民主的方式吗?就好像它只不过是另一个你必须服从的体制?
她微笑着耸耸肩:“从前,主任经常大肆鼓吹社会主义,这个队伍,那个队伍。而现在鼓吹的是自由市场经济。他完全转了180度”。但她对此并不感到惊讶或者愤慨:“我们管这叫随波逐流”。
“而现在”,我说,“你正在学习自己游泳”。
“是的,现在我正在学习自己游泳”,她脸红了,“我现在在公开场合讲话。是的,我做到了。”
她参加过一个关于行业未来的座谈会,“我听到我们总理说,萨克森如何如何,纺织厂这个、纺织厂那个,我对自己说,应当让他知道工厂里实际的情况是什么样”。
于是在他演讲之后的间歇里,她喝了几杯白兰地,然后,会议恢复进行时,她站起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那是我第一次有足够的勇气演讲”,她看了看我,腼腆地笑了,再次耸耸肩,惊讶于自己身上发生的事。“现在我在每一个地方都讲话,即使是在市集广场上”。
至少,Schindler 夫人不是活在民主 “之下”,而是第一次活在 “其中”。

做一个好德国人
从前,它叫 Dimitrov 学校。这儿有一座雕像,纪念这个1934年因国会纵火案而受到审判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学校操场上甚至曾经有过一个社会主义风格的 Dimitrov 雕像,但已经被推掉了。这个位置现在什么都没有。
革命之后,它改名为雷克拉姆学校,以在纳粹和民主德国时期都受到压制的自由思想出版社雷克拉姆为名。
我在地下室的学生房间里,这儿革命后被刷新过,一面墙上用英语写着:“嘿,老师!别干涉孩子们!” 17岁的 Martin Moschek 正在告诉我从前的课程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在数学课上,我们要计算这样的问题:古巴被帝国主义者攻击,5个人驻扎在一个防空火箭站。我们要计算导弹的弹道抛物线,它是否能击中帝国主义者。诸如此类”。想到这里,他摇了摇头,“那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这有什么奇怪的”。
Martin 的父亲是一名路德教派牧师,所以 Martin 的成长有一半是处于当局的意识形态玻璃罐之中,另一半在其外。
回头来看,他不知道有多少同学相信他们被教授的东西,抑或是默默地在内心 “移民”。
对他而言,回头看确实难以相信学生们曾经如此顺从。他高兴地笑了,用他那种平静、正式、带点学究气的方式说:“学校没有学生,就不成其为学校,这一点得到更多认可了”。所以一个英国摇滚乐队的智慧被涂鸦在他身后的墙上。
(译者注:”嘿,老师!别干涉孩子们!” 这是英国著名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的歌曲《墙上的另一块砖》中的歌词)

As with Milošević of Serbia, Ceauçescu in Romania, or Husák of Czechoslovakia, Honecker in Germany turned to nationalism to mask the senility of his regime. Too late, too late. In November of 1989, the people decided that they, not the state, were the true nation.”
Martin 有一张光滑的、天使般的脸,卷发的轮廓像是在丢勒的画中。他柔和、深思熟虑的说话方式带有德国路德派的深沉内敛。我问他,从前,民族主义意味着什么。
“我以身为民主德国的公民而自豪,我以我的祖国而自豪。我们总是把祖国和民主德国联系在一起 —— 没有德意志”。
同样的东西,Börner 先生说得更多。对于在民主德国成长起来的每一个人,“德意志” 都是一个不可置信的幽灵,一个演讲中的形象,只在巴戈利亚啤酒馆复仇式的东德怒骂中、或民主德国电视台的话语中使用。
不论如何,1939年的旧德意志,那个扩展到远至今天的波兰、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已经被英雄般的苏联军队所粉碎。它已经永远消失了,埋葬在盟军和苏联的联合占领之下。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将会创建一个社会主义自身的、工人运动组织及其符号 —— 尖锐的、冷漠的科学量角器 —— 相联系的德国。
然而,精英并没有放弃,如果将某些民族象征复活、翻新,对国家的忠诚会更为丰富。
20世纪70年代,宣传部组织了对德国传统英雄谨慎、有限的运用。那个反抗德国王公的路德被允许进入万神殿;而那个为德国王公叫嚣、要镇压1525年农民反抗的路德,被小心翼翼地从图景中抹去了。
军纪严明的腓特烈大帝赢得了官方的尊崇,因为当局对军纪比对社会主义更为看重。
与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胡萨克一样,昂纳克的德国也转向了民族主义,以掩盖他的政权的衰朽。
太迟了,太迟了。1989年11月,人民做出了决定,是他们,而不是国家,才是真正的民族。
那么,一个17岁的东德人如何理解现在的德意志民族概念呢?
Martin 思考了很长时间,然后静悄悄地说:“如果现在你说你是一个民族主义者,那么很清楚 —— 至少对于我是这样 —— 你是在说,你为你的国家而骄傲。就其自身而言,并不是一件坏事。问题在于,它并不会就此止步。它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这里有些人说,统一尚未完成 —— 波兰的东部领土和苏台德区还在等着。那像是敲响了我体内的警钟”。
他又思考了一会,然后说:“全都可以归结为暴力。如果一个人说他为德国自豪,不带暴力地劝说我,那还好。不幸的是,现在在德国,这很少见”。

黄昏,Martin 和我正穿过架在莱比锡郊区一条运河上的一座狭窄步行桥。我忽然注意到,在桥上有黑人从我们身边经过。北非人、巴基斯坦人、索马里人,一对对的,手里拎着塑料购物袋,夹克的领子竖起以抵挡风寒。
他们是我在莱比锡见到的第一批非白人面孔。像东欧大部分地方一样,东德是白人占绝对多数。
从东德的角度来看,在统一带来的所有惊奇中,最让人惊讶的是种族。法兰克福这样的城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国外出生。在每一个人群中,都会有一片这样的面孔的海洋。
在莱比锡,他们是新奇的、陌生的、异类的。他们在这座桥上,因为那是回家的路,而他们的家是一个提供庇护的旅店、一群活动房屋,设置在细铁丝栅栏后面的砂石地上。紧邻柏林至莱比锡的高速公路。
我们用法语和一些年轻的阿尔及利亚人交谈。他们走遍了欧洲,寻找工作,他们已经申请在这里避难,正在等候处理。
但这是场痛苦的等待。他们说那些活动房又冷又透风,晚上他们躺在铺位上,抽着雪茄烟,等待纳粹分子的攻击。
Martin 点头同意。他们不是在夸大其词。两个星期前,光头党第一次在桥上出现,向旅店走去的时候,他和一个学校的朋友正在这里。
光头党的人带有刀子和棒球球棍。桥的另一边,警察坐在一辆大众的巴士里面,并没有阻止他们。
因此 Martin 和朋友试图阻止这些光头党穿过桥梁。两个文质彬彬的少年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没有想过带上武器。没有任何想要打架的意思。他们想,只要勇敢地站出来,就可以把一群光头党打发走。
Martin 悲哀地笑了笑,像是在抚摸一个旧的伤疤:“我们被拳打脚踢,他们试图把我们扔到运河里”。
最后,警察终于跳下车子,把这些人赶走了。Martin 靠在桥栏杆上,注视着活动房。我问他为什么认为自己应该介入?这些人是来真的,他们有武器,这不是少年的地盘。
他想了想,然后说他知道 —— 因为父亲告诉过他 —— 20年代魏玛时期,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暴力循环不断升级,直到最终完全失控。然后,他盯着坐在活动房门口抽烟的黑人,“看,我只是想显示,在这里仍有一些人支持他们”。
“我想要那些光头党知道,如果他们再来袭击这些人,他们必须先越过一个德国人”。⚪️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