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您有没想过,当一个社会出现抑郁症/精神类疾病爆发时,这种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
十年前的2012年,上海市卫生局曾经颁布了一份《精神疾病防治服务规范 (2012版)》,规定将开展 “疑似精神病患调查”。对于所谓的有过自杀或者自残、经常胡言乱语、无故不上学、不上班、不出家门、不和任何人接触等 “行为异常” 的人员,将作为疑似精神病患者的调查线索。
一时舆论大哗。在过去的十年,这则消息每次被翻出来都能重新引发一轮议论。公众很难相信这样一个随意、泛化的精神病标准竟然是认真的。尤其是,随着上海新冠疫情下的强制封城和反复筛查,后疫情时代的上海俨然呈现一幅全民精神病态的城市面貌。
本文将要介绍的这两本新书所论述就是临床意义上的精神疾病,也就是您说了解的 “确诊” 患者,他们的痛苦真正曝光的东西是什么。
记得IYP的 列表-5 在简介中写到的那句话?—— “直接行动是最好的疗愈”。
📌 您可以在这里下载这本书:https://www.patreon.com/posts/bie-zai-chi-yao-70286123
📌 如果您错过了(2017年):
1990 年,乔治·布什总统宣布,“新的大发现时代” 已经显露 “大脑研究的曙光”。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美国政府向脑科学领域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期望彻底改变人们对精神疾病的理解,从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到精神分裂症。科学家们设想,未来的精神疾病将可能通过基因测试、简单的抽血或大脑扫描就可以得到诊断。新药将针对特定的神经化学失衡,进行更有效的治疗。布什宣称,1990 年代将被称为 “大脑的十年”。
这个有关大脑研究的美丽新世界,也承诺让人们摆脱几个世纪以来与精神疾病和成瘾相关的耻辱和歧视。将精神疾病定位在大脑中,等于视同如糖尿病和高胆固醇一样的慢性疾病,而不是个人的道德缺陷或性格缺陷。虽然无法准确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但人们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精神病学将如布什所说的,破解这个 “不可思议的器官” 的 “奥秘” 和 “奇迹”。
精神病临床的现实远没有那么迷人
作为一名精神病学家和历史学家,回顾这一切的时候,我发现这些曾经的希望给人很古怪的感觉。它们让我想起了 二十 世纪人们对技术未来类似的错位愿景,譬如飞行汽车、满足一天营养的药丸。而精神病临床的现实远没有伴随我成长的愿景那么有魅力。 30 年后,我们仍然没有针对精神疾病的生物试验,没有任何进行中的测试。相反,我们的诊断完全基于一本书中的标准,即《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通常被自嘲为美国精神病学的 “圣经”)。在过去的 70 年里,它修订了五版,虽然最新版比旧版多了近 100 页,但根本看不出它哪点儿比旧版本更好。没有一个诊断是按照大脑情况做出的。
我们在治疗方面也没有任何重大突破。几十年来,制药业已经生产了数十种抗抑郁药和精神类药物,但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比 1950 年至 1990 年间出现的药物更有效。今天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更有可能无家可归或过早死亡。在过去 150 年的任何时候,精神病人的寿命都要比一般人口少 10 到 20 年。生物学研究也未能揭示为什么精神科药物可以帮助一些患者,但不能帮助其他患者。当病人问我抗抑郁药的作用是什么时,我不得不耸耸肩, “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我们只是有根据知道它有大约 30% 的可能性会帮助你改善情绪”。一位患者困惑地回答说,“这不是和神经递质有关吗?” 我叹了口气,“是的,有一段时间里理论是这样的,但它没有成功。”
还有污名化的问题。正如人类学家海伦娜·汉森(Helena Hansen)所说,研究成瘾的神经科学往往强化了污名化,他们把精神疾病的实质还原到个人问题上,而不是作为源于种族暴力等等长历史的、结构性因素的结果。与白人患者相比,美国精神科医生诊断出黑人和棕色人种的精神分裂症发病率与其人口不成比例。精神科医生兼社会学家乔纳森·梅茨尔(Jonathan Metzl)将这种差异追溯到 1970 年代,在民权运动高涨后的精神科医生们把黑人激进主义病态化为 “精神病”。然后,经历心理健康危机的黑人患者,包括儿童,更有可能遭受身体约束的暴力,以类似于一个多世纪前收容所对待疯子的方式被绑在床上。
2015 年,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 (NIMH) 前所长托马斯·英塞尔 (Thomas Insel) 吐露了这种幻灭感:
我在 NIMH工作了 13 年,致力于精神疾病相关的神经科学和遗传学,当我回首往事时 …… 我意识到,虽然我成功地让貌似很酷的科学家们以极高的成本发表了许多非常酷的论文 — — 花费大概是 200 亿美元 — — 但我不认为我们真正减少了自杀、减少了住院、帮助了数以千万计患有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复。
但这对今天的精神病学术界意识到与实际的脱节毫无帮助。在瘟疫流行下的社会孤立、社会中的种族暴力、以及在学校、体育运动和市场经济日益激烈的超级竞争文化中,许多人都越来越关注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但精神病的学术研究几乎只关注大脑研究,这意味着精神疾病的专业问题本身在这些研究对话中基本上消失了。这是为什么?所有关于神经生物学的 “酷论文” 都获得了学术资助并帮助教授升了职,但它们并没有对数百万罹患精神困扰的人们的诊断和护理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影响。
我们是怎么发展到如此田地的?如果我们不能从生物学上理解精神疾病,那么当我们从历史角度审视它们时会发生什么?精神病史家最近出版的两本书探讨了生物-精神病学的危机,追溯了导致精神病学家试图将精神疾病的现实 — — 以及该职业的合法性 — — 与大脑联系起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和专业因素。这些都是大书,由精神病学史学家撰写,其分量和范围都涵盖了该行业 200 年的失败。它们揭露了美国精神病学在其历史上一直如何很容易受到炒作和追求 “酷” 的影响,从 1890 年代对大脑解剖的热情到一个世纪后围绕神经递质和遗传学的大肆炒作。
了解精神病学中有关炒作和危机的跌宕历史在今天至关重要,因为该行业正朝着下一个趋势发展:迷幻药,已经被誉为 “复兴” 和精神病的 “下一个前沿”。这两个历史著作所表明的,学术界和企业对炒作的追求忽视了受精神病研究和护理影响的最大社群的视角,带来他们重大的心理和身体伤害。从这些书的优点和局限性出发,可能促使精神病学家们重新考虑其优先事项。其挑战结果,让我们去重现构想一个未来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花费在生物研究的数十亿美元应该被重新分配给最需要它的社群,不是以大脑为中心,而是为以整个人类为中心的护理形式提供必要的资源。
精神病学很容易受到炒作的影响,精神病学科史则充满了投机市场一般的兴衰起伏
在《心灵修复者:精神病学对精神疾病生物学的艰辛探索》一书中,作者安妮·哈灵顿认为,当前的危机只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精神-生物学的一系列失败中的最新一次。 在这项全面的研究中,精神病学史就像投机市场的繁荣和萧条一样起伏不定。 最初的浪潮随着精神病学的革命性突破而起,伴随着将改变已有精神病学的热望。然后,浪潮崩溃了,因为精神科医生没能兑现这些大胆的承诺。 当危机接踵而至,下一波精神病学革命又开始形成。历史就是如此反复冲刷。
哈灵顿追踪的美国精神病学第一次的 “革命” 出现在 19 世纪。当时,大型精神病院占据了精神病院的主导地位,例如纽约市今天被称为罗斯福岛的布莱克威尔岛医院。这些机构旨在通过将精神障碍患者置于专门的收容所内 “治愈” 他们。然而,一系列新闻曝光显示,这些收容所人满为患,资金不足,患者生活在悲惨的环境中,并没有基本的治疗条件。例如,1887 年,笔名 Nellie Bly 的记者伊丽莎白·希曼(Elizabeth Seaman)在布莱克威尔岛医院(Blackwell’s Island Hospital)卧底,然后通过《疯人院的十天》一书中揭露了可怕的暴行,这本书也称为当时的畅销书。疯人院-收容所模式的精神病学面临着公众信任危机。
随后,如哈灵顿所解释的那样,欧洲的神经解剖学家前来援手。与收容所医生不同,解剖学家对治愈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基于优生学理论,他们认为收容所内的患者是 “退化者”,在生物学上不适合应对现代生活的压力。但他们也相信,精神病患者可以把他们的大脑提供给科学事业,在他们死后继续为社会提供服务。解剖学家希望,解剖他们的病态大脑可以揭示精神痛苦的生物学原因。
在 19 世纪后期,随着精神病收容所从治疗机构转变为研究场所,在未经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医院对大多数贫穷患者的身体和大脑进行了数千次解剖。然而哈灵顿的总结是这些解剖并没有揭示什么。问题在于这些神经解剖学家不知道他们在寻找什么。精神病学家 Karl Jaspers 将这些解剖学上的努力概括为一个 “大脑神话”。神经解剖学的解剖很失败。
放弃了神经解剖学家的治疗虚无主义,生物精神病学的第二次推动转向了另一个极端。 20 世纪初的美国是一个肆无忌惮的时代,精神病医生对病人的身体以近乎绝望的实验寻找治愈方法。安德鲁·斯卡尔(Andrew Scull)的新书《绝望的补救:精神病学治疗的动荡探索》,对这个 “实验狂欢” 的时代描述得令人毛骨悚然。虽然与哈灵顿的研究重叠了相同的历史背景,但斯卡尔更生动的叙述表明,生物精神病学的基础是建立在对妇女、穷人和有色人种身体施加的暴力之上。 Scull 认为,从 1910 年到 1950 年间,美国的研究人员把那些可怜的患者 “看作客体,而不是有着情感的生命”。当时的患者几乎没有任何法律权利,没有办法抗议医生对他们的身体进行侵入性和随意的实验。
以美国精神病学家亨利·科顿为例,他出现在哈灵顿和斯卡尔的叙述中。在 1910 年代和 20 年代,科顿确信所有的精神病都是由感染引起的,也就是感染的结果,他的理论建立在一种较早病症的假设上,即梅毒螺旋体进入大脑后引发的 “精神失常的全身瘫痪”。基于这种未经证实的脓毒性精神病理论,科顿得出结论,可以通过手术切除患者体内潜在的感染源来治疗精神病。科顿以治愈精神病的名义手术切除了牙齿、阑尾、卵巢、睾丸、结肠等,导致数千名患者致残和死亡。后来发现科顿的结肠切除术的死亡率超过 44%,其中女性所占比例畸高。
Scull 研究的另一个例子是维也纳医生 Julius Wagner-Jauregg,他认为诱发高烧和抽搐可能有助于精神病患者。 1927年,他因利用疟疾诱发高热来治疗全身性瘫痪的精神病人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哈灵顿指出,在华盛顿特区著名的圣伊丽莎白医院,某些在社会上最边缘化的慢性精神病患者变成了“疟疾储备”,他们的体内储存着寄生虫,为其他患者的治疗做准备。
Scull认为这一时期最极端的实验莫过于额叶切除术。这一流程开始时是对头部进行局麻,钻穿颅骨,并用刀片切割大脑的额叶。当病人开始感动“困惑”时,外科医生便停止切割。这项创新为葡萄牙神经学家 Egan Moniz 赢得了 1949 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在美国推广该手术的沃尔特.弗里曼后来又创新了一种方法,将冰锥从眼窝插入大脑。在 1940 年代和 50 年代,成千上万的人进行了额叶切除术,其中针对女性的手术同样比例畸高。弗里曼将手术的效果描述为将他的病人变成像“家庭病人或家庭宠物”,让家庭和机构更容易控制他们的行为。
绝育是这一时期美国精神病治疗中流行的另一种侵入性手术。根据旧的退化理论,绝育是一种优生而非治疗工具:它旨在防止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传递他们的“垃圾股”。在 1927 年臭名昭著的巴克诉贝尔案中,这种道德上令人担忧的做法进入了最高法院,当时的助理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辩称,社会有理由寻求“防止那些明显不适合的人延续他们的种类”。在该决定之后的十年里,约有 28,000 名被诊断患有“弱智”的美国人被做了绝育手术。
Scull 和 Harrington 得出结论,今天的精神病学从这段疯狂、危险的实验中继承下来的唯一有效治疗方法是电惊厥疗法 (ECT)。 1930 年代,匈牙利精神病学家拉迪斯拉夫·梅杜纳(Ladislav Meduna)(错误地)相信癫痫发作和精神分裂症是两种对抗性疾病,他试图用强效兴奋剂美甲唑(Metrazol)诱导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癫痫发作。由于治疗过程中的野蛮暴力,大约 40% 的患者发生了脊柱压缩性骨折。尽管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疗法进行了调整,以期对患者更安全,而最终演变成 ECT,今天继续在美国精神病治疗中使用。目前的研究表明, ECT 在治疗抑郁症方面是安全有效的,但和 1930 年代的研究人员一样,我们仍然不知道它为什么或如何起作用。
下一批精神病学的革命者,则拒绝这种对身体的暴力实验,转而采用一种关注心灵的方法:精神分析。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于 1909 年抵达美国,但他的想法直到二战后才在这个行业中站稳脚跟。从那些遭受战场精神创伤的士兵身上,精神科医生最终明白了战争的心理创伤可能与他们的身体伤害一样具有毁灭性。
如果您错过了《背叛主流?精神病院欢迎你:被病理化的异议》
在战后,精神分析逐渐形成了精神病领域里斯卡尔所谓的 “脆弱霸权”。哈灵顿强调,精神病学家转向弗洛伊德是因为他们相信它为精神疾病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医学方法: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干预,患者的无意识当中包含着解释和治疗精神病患者的症结。
到 1950 年代,美国大多数精神病住院医师培训项目由精神分析学家领导,许多有影响力的精神分析家以诋毁早期的躯体治疗来巩固他们的专业能力。例如,1948 年,一组有影响力的分析人士认为,额叶切除术不是一种疗法,而是一种 “专门破坏” 人类所必需的大脑部分的 “人造自我毁灭性手术”。流行文化中的意见领袖也将精神分析视为美国社会面临的更广泛问题的解决方案。在 1948 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年度会议上,哈里·杜鲁门总统表示,“精神病学领域的专家” 对于维护美国的 “理智” 至关重要,这是 “和平的最大先决条件”。
但就像之前历次革命的荣衰周期,精神分析也未能实现其过于雄心勃勃的目标,而且精神分析几乎完全专注于思想,这并不能减少精神疾病对弱势群体造成的伤害。在 1970 年代,同性恋活动家大声抗议美国精神病学将他们的性行为病态化。这些活动家,包括一些研究同性恋的精神病学家,冲进了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PA)的年度会议,并成功地要求从精神病目录中删除同性恋。
1970 年代同性恋、女权主义、黑人力量和残疾运动的积极分子面临的问题是,制度性的精神分析拥抱和接受的是让个人接受白人、有能力者、异性恋和中上阶级的道德规范。 对于那些挑战这些规范的认同来说,心理治疗更有可能造成伤害而不是治愈。
正如芝加哥同性恋解放阵线的成员在 1970 年写给美国医学协会的传单中所宣称的:
我们同性恋解放的同性恋者认为,治疗的调整学派不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方法 . . . 女性的心理健康并不意味着对女性的治疗 — — 它意味着消除男性至上主义。 不要再不治疗黑人了,而是要结束种族主义。 穷人也不需要精神科医生(25 美元一次开个玩笑!),他们需要的是财富的民主分配。 离开沙发,走上街头!
他们呼吁离开沙发走上街头,是对主要由白人组成的学术性精神分析职业的控诉,这一职业已经具体化了,而不是挑战社会的压迫结构。例如,本世纪中叶的许多分析家认为,黑人不具备在沙发上进行精神分析所需的心理复杂性。此外,历史学家马丁·萨默斯(Martin Summers)表明,在治疗黑人患者的机构中,即使面对有悖这一教条的数据和临床经验,精神分析学家也会强调 “独特的黑人心理” 这一古老的种族主义刻板印象。
可以肯定的是,在 19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政治狂热中出现了更激进的精神分析愿景,但你必须超越 Scull 和 Harrington 的叙述才能找到它们。例如,在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尔,出生于马提尼克岛的精神病学家弗朗茨·法农 (Frantz Fanon),他批评了殖民主义的反黑人暴力,也构想了更多解放形式的精神护理。在拉丁美洲,我自己的工作着重于 1970 年代初期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如何想象一种 “被压迫者的心理治疗”,将心理健康与摆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社会和政治解放联系起来。但是,这些在第三世界的激进努力,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与这两本书中讨论的主流精神分析相去甚远。
对 Scull 和 Harrington 来说,对美国精神病学合法性的最大打击可能来自该行业本身。 1973 年,法医精神病学家大卫·罗森汉 (David Rosenhan) 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名为 “在疯狂的地方保持理智” 的实验。他的这篇著名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精神科医生无法区分理智与精神错乱。在实验中,罗森汉派了八名假装听到 “空虚”、“沉闷” 和 “砰砰” 等词的 “假病人” 到精神病院进行采访。罗森汉发现八人都被精神科医生送进了医院。他们的平均留院时间为十九天。除一名患者外,所有患者在出院时都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虽然记者苏珊娜·卡哈兰(Susannah Cahalan)最近揭露了罗森汉捏造实验结果,但当时这篇论文动摇了这个专业的基础,打破了精神分析对该领域的脆弱控制。
进入 1980 年代的生物精神病学家,他们为我们今天所处的生物革命奠定了基础。部分为了回应罗森汉的研究,这个新的精神病学家联盟将职业合法性危机归咎于精神分析。他们认为,它的蒙昧主义理论充斥着行内黑话而不是实质内容,已经把美国的精神病学变成了巴别塔,精神病学家之间几乎无法进行有意义的交流。早在 1960 年代的研究表明,精神科医生的诊断在统计学上并不可靠 — — 也就是说,即使在评估同一名患者时,精神科医生也经常在诊断上存在分歧。有影响力的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斯皮策(Robert Spitzer)认为,解决办法是从根本上改革一本大多数专业人士忽视的书:DSM。斯皮策和 DSM-III 工作组重构了手册的精神分析基础,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认为可以用于指导治疗和研究患者行为的可观察的参照,也就是对每种疾病的明确和客观的标准。
1980 年第三版 DSM 的出版,预示着被明确称为精神病学 “生物革命” 的诞生。这场革命的证据,标志着斯皮策和其他人对精神药理学的发展,是1954年引入的第一个有效的抗精神病药物氯丙嗪,以及其后对神经递质和遗传学作用的生物学研究。他们相信,对大脑和身体的研究最终会将 DSM-III 中行为描述的疾病与其潜在的生物学原因关联起来。
我们现在知道,这种被寄予厚望的科学前景从未到来,精神病学一直在等待它的生物学戈多。虽然 DSM-III 和后续版本(包括 IV 和 V)提高了诊断可靠性,但精神病学仍然存在有效性问题。换句话说,在 DSM 中定义每种病症的症状集合 — — 经过数十亿美元的投资 — — 仍然与我们的大脑、血液或基因的剧烈变化无关。
例如,经常被引用的声称精神分裂症具有遗传基础的说法并未通过科学验证。正如 Scull 所讨论的,在未能找到一组可以解释精神分裂症的孟德尔基因后,2000 年代的研究人员将希望寄托在新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 (GWAS) 上,该研究可以筛查数十万个碱基对、寻找精神疾病的遗传基因。但 GWAS 研究并未揭示精神分裂症(或双相情感障碍)的明确遗传基础。虽然结合数百个遗传位点至多可以帮助解释观察到的精神分裂症8%的变异,但一个人仍然有可能拥有这些遗传变异而不会患上这种疾病。著名的精神病学家 Michael Rutter 和 Rudolf Uher 的反思是:“对精神疾病的分子遗传学研究做了很多工作,但发现却很少。事实上,在全基因组关联研究的时代,精神疾病已经与大多数类型的身体疾病区分开来,因为它们缺乏充分的遗传关联。”
转向生物学并没有对治疗产生有意义的影响,但它作为一种心理药物的营销策略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虽然转向生物学并没有对诊断或治疗产生有意义的影响,但它作为精神药物的营销策略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事实上,过去半个世纪精神病学最大的变化可能是大型制药公司的诞生,而不是生物学的任何革命。精神症状市场在 1980 年代对制药公司的吸引力至少存在两个原因。首先,精神药物是长期服用的:许多患者是终生消费者。其次,自我认知和主观体验在精神疾病的诊断中起主要作用。制药公司高管意识到,这一事实意味着需求可以受到有效营销的影响和操纵,将精神药物定位为消费者对其生活不满的解决方案。
1990 年代,制药公司投资数百万,利用精神病学家的生物学热情制作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广告。这些广告颇具误导性地声称,他们的药物针对的是大脑中的 “化学失衡”,这种失衡会导致美国人日常的抑郁和焦虑感。除了消费者需求外,该行业还将其相当大的影响力集中在处方者身上。制药公司在著名的学术中心为有影响力的医生提供药物样品、利润丰厚的咨询服务和其他激励措施来兜售他们的产品。
今天,该行业在财政上支持几乎所有精神病学期刊和学科会议。DSM-V 工作组中有差不多 69% 的成员披露了与制药行业的财务关系,这要比 DSM-IV 工作组报告的披露还多 21%。制药公司对 DSM 的影响促进了诊断类别的扩展,“精神疾病” 的概念本身因此变得更具包容性,从而扩大了潜在药物市场的规模。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制药公司还影响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对药物的审核。如今,FDA 46% 的预算来自提交药物申请的公司(所谓的 “行业使用费”),公司负责对其生产的药物进行安全性和有效性试验。这种明显的利益冲突导致制药公司歪曲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证据、隐藏负面结果和副作用数据,并雇人捉刀学术文章。虽然许多重大的民事和刑事裁决已经对这些违法行为的公司进行了处罚,但这种不道德行为的结构性根源 — — 行业评估其获利产品这一事实 — — 仍然存在。
大型制药公司对行业的重大影响,从对美国精神病医生的身份认同的改变就可看到,他们已经从上世纪中叶的精神分析师转为今天的药物处方师。虽然研究表明心理治疗与治疗焦虑症、抑郁症和其他疾病的药物一样有效,甚至更有效,但精神科医生通常专注于药物处方,并将患者送到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那里接受治疗。这种转变取得了可观的回报。今天的精神药物行业价值近 600 亿美元,去年有六分之一的美国人服用了精神科药物。
然而,制药业在精神病学上投入如此之大,为什么药物治疗却一直没有突破呢?一个主要原因是该行业在精神科药物广告上的花费比新药研发上多出数十亿美元。正如精神病学家大卫·希利(David Healy)所表明的那样,专门用于研发的资金通常并非旨在产生真正的创新。自 1990 年以来生产的几乎所有精神药物都是旧的仿制药的 “模仿者”,只是进行了轻微的化学修饰。这些(不幸地被命名为)“me-too” 的药物在临床上的效果并不比之前的药物好,但它们轻微的生化新颖性意味着它们可以申请专利,这样制药公司就可以向医疗保险公司收取高额费用。
也许最坏的消息是,已经创造并利用了精神病学市场的大型制药公司现在纷纷跳船。人类学家乔·杜米特(Joe Dumit)表明,大多数精神科药物很快就面临专利失效,医药公司将被迫降低收费。由于充满仿制药,而且看不到重大的生物科学的突破,市场的增长空间突然变得很小。几乎所有主要的制药公司都决定退出精神药物研究,转向更有前景的领域,尤其是“生物制剂”和其他抗癌药物的开发。
那么,精神病学有前途吗?制药业在继续发展,除了精神病学需要谦逊的模糊声明以及精神病学家应该关注社会心理治疗方法而不仅仅关注生物学治疗方法的信息,Harrington 和 Scull 也没有提供什么解决方案。
Scull 还想知道回归心理治疗是否可能是答案。当今美国的精神科门诊通常依赖 15 到 30 分钟的简短访问,集中在药物管理和症状检查清单上。 Scull 对精神科医生和病人之间的这一联系的感到悲哀,上世纪中叶的精神科医生代表着患者(大部分颇有中上阶级的特权),至少做精神分析需要倾听患者,他强调说。
不幸的是,过去五十年的心理治疗越发变得像药丸本身:标准化、快速、公司化和廉价。在 1980 年代和 90 年代,医疗管理放大了一些精神病学家的批评,即密集和探索性质的长期精神分析意味着对时间和金钱的大量投入,但是收益不大。他们提倡更快、更实惠的医疗形式,不仅包括药物,还包括新的认知行为疗法 (CBT) 技术,其结果如历史学家 Hannah Zeavin 所言,这些技术贬低了治疗师本人的治愈能力。某些 CBT 方法试图将治疗师的角色缩减到照本宣科,如同为患者编写的计算机程序中的自动对话和人工程序。在 CBT 模型中,患者的思想和感受被理解为可以编程的脚本,而内省和心理洞察力 — — Scull 所重视的 “倾听” — — 被一些从业者诋毁为 “肚脐凝视”。这导致传统的精神分析在今天几乎不可能实现了。虽然许多治疗师采取折衷,借鉴 CBT 和其他各种临床精神分析方法,但传统精神分析所代表的那种长期的、开放式的治疗现在极难获得。医疗保险公司拒绝承保,想要进行精神分析的患者经常被迫自费支付高额费用。
随着精神分析的衰落,精神和心理治疗越来越像企业自动化了。如今,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经常在 Talkspace 之类的数字平台上寻找 “零工” 机会,赚取大约 25 美元的时薪,几乎无法控制他们的工作时间、费用或工作条件。其他人则使用人工智能(通常是女性化的)聊天机器人进行治疗。令人不安的是,这些数字程序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监管,其治疗标准很可疑。鉴于医疗保险公司的财务压力和要求患者尽快康复的卫生系统,坦率地说,心理治疗的未来看起来很黯淡 — — 无论是对渴望恢复与人接触能力的患者,还是对劳动力价值被贬低到随时被自动删除的治疗医师,都一样。
精神病学视野中唯一真正令人兴奋的发展,似乎是迷幻药,哈灵顿在她的结论中非常简短地提到了迷幻药。非营利组织和科研人员目前正在对 MDMA(摇头丸)、psilocybin(神奇蘑菇)、LSD(麦角酸)、美斯卡林、伊博加因和死藤水进行了50 多项的 FDA 试验,用于治疗各种精神疾病。艾氯胺酮已被批准用于治疗难治性抑郁症。研究人员和记者,如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称之为“迷幻复兴”,认为这些迷幻药物将彻底改变精神病学,开启对思想和大脑之间联系的新理解,并帮助成千上万的患者。
但这听起来是不是太熟悉了? “迷幻复兴” 感觉就像是下一次哈灵顿革命,依旧是夸夸其谈的主张、海量资本进入,以及此刻对患者来说尚不确定的好处。关于这些药物的疗效仍然没有定论,但已经很清楚的是,制药行业已经注意到了。 2020 年,总部位于伦敦的 Compass Pathways 获得了Thiel Capital 的种子投资,成为第一家上市的迷幻药公司,IPO 后估值为 11 亿美元。
不容忽视的是,大型制药公司没有放弃其惯用伎俩。正如我曾经指出的,强生公司对使用氯胺酮治疗抑郁症很感兴趣,但无法为该药申请专利,因为它已经是一种廉价的仿制药。强生决定做一个模仿者,用化学方法分离出化合物的一个镜像。他们将这种“me-too”的化合物称为Spravato,并为这种药物申请了专利,现在每剂收费近 1000 美元。商业公司们正在使用类似的策略从土著社区沿用几个世纪的、具有精神活性的植物药中分离出可申请专利的化合物,这引发了人们对新兴迷幻药行业的伦理担忧,即欧美对土著知识、植物和土地的永久剥削问题。
因此,这种 “迷幻复兴” 很可能只是始于 1980 年代的大型制药公司其更大规模革命的新阶段。无论迷幻药最终提供何种临床益处,药物都不能解决困扰我们心理健康系统的结构性问题。继续获利的是大型制药公司以及与行业合作的精神病学家。迷幻药只能帮助那些我们的社会中能够接触到它们的人:主要是拥有私人保险的白人和中上层阶级。
这两本书打开了一个未来的想象,可让投入生物-精神病学研究的数十亿美元被重新分配给最需要它的社群
虽然这两本令人印象深刻的书都抓住了重要的历史背景,但它们也错过了一些对精神病学过去的批评,这让他们对未来的看法多少有些局限:他们未能直面精神病体系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对黑人社区的大规模监禁中所扮演的角色。
对 Harrington 和 Scull 来说,随着大型精神病院的关闭和去制度化的兴起,也就是1960 年代开始将精神护理从精神病院转移到社区的运动,可以说在人口层面上,精神病学的监狱模式基本终结了。在这种常规叙事中,去制度化的问题被新自由主义所忽视:患者从精神病院大量出院后却得不到多少资源和支持,导致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大量流离失所,流落街头的比率很高。
当然,这个故事忽略了监禁模式与精神病学交织缠绕的沉默和微妙。正如历史学家安妮·帕森斯(Anne Parsons)所说,“收容病院模式并没有随着去制度化而消失”。相反,“它以现代监狱工业综合体的形式回归。” 今天,美国一些最大的心理健康机构在监狱中开展业务 — — 美国监狱中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比监狱之外精神病院中的总人数还要多。大约 40% 被诊断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不得不在监禁状态下度过余生,大多数案例都是种族主义政策下正在进行的毒品战争的结果。监狱中的精神病患者处于高度隔离状态下。虽然精神病院倾向于收留白人、中年病人,但监狱却不成比例地关押了大量四十岁以下的黑人精神疾病患者。
此外,社会学家 Anthony Ryan Hatch 认为,监狱内精神药物的使用被允许对患者在大脑层面施行控制。监狱政策的专家们没有将精神药物定义为医学治疗,而是将其视为 “技术性矫正” 的重要组成部分,即通过 “新技术的战略应用,降低大规模监禁的成本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囚犯对社会的风险”。 例如2000 年,大约 95% 处于最高或高度戒备状态的监狱都向被监禁者分发精神药物。
这些书中之所以缺少这些事实,缘于哈灵顿和斯卡尔过分专注精神病的学术精英,一个总是避免触及监狱工作的群体。正如 Hatch 所指出的,我们几乎所有关于精神药物的公共知识都来自未监禁者的使用,而关于监狱精神药物的知识往往与囚犯本身一样受到严密保护。这种沉默是一种压迫形式,既掩盖了将精神药物用作监管控制技术,也掩盖了我们未能为囚禁中人(其中许多人因监禁而受到创伤)提供他们应得的人道待遇的事实。
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我相信构成这一悲剧的,是代表精神病领域的我们的沉默和缺乏责任感。尽管精神疾病患者人群的预期寿命不断下降,被监禁和无家可归的精神病患者比例很高,并且经历了范式的失败,但生物精神病学的研究机器仍在不断发展。
在他自己的新书《治愈:我们从精神疾病到精神健康的道路》中,作者 Insel 认为生物精神病学过去的失败表明我们应该 “加倍努力进行大脑研究”,而不是犹豫哪个优先。 Insel 在 NIMH 的继任者 Joshua Gordon 一直保持该组织对生物精神病学研究的关注,当然只是狭义的。 虽然 Harrington 和 Scull 都指出了今天精神病执业的 “危机”,但更可怕的事实是,学院中的许多人都在照常进行。 换句话说,精神病科学的真正危机在于没有危机。
如果上述这些精英的学术临床医师的历史没有澄清整个问题,就不会产生有想象力的解决方案。寻求答案本身需要让学术界去中心化,并在标准精神病学科史之外寻找那些被忽视的叙述。例如,残疾活动家和学者 Liat Ben-Moshe 的历史著作转向了 “疯人社区”,在这些社区内部,人们没有将神经分裂看作一种需要治疗的医学问题,而是一种大可庆祝的身份。 1970 年代的 “疯人活动家” 和专业联盟,如反精神病医生 Thomas Szasz,成功地要求在美国社会废除暴力的精神病院和囚禁精神病人的做法。虽然这场要求精神病学去制度化的运动并没有带来美国残疾人的全面解放,但 Ben-Moshe 认为,它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即社区如何才能够成功抵制以治疗之名对结构的压迫。
Ben-Moshe 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批判性地审视过去的精神暴力,而且还提供了一个她所谓的 “谱系”,观照似乎无法想象的未来。抵抗的谱系对 “健康” 的概念化,不是基于学科医师提供的个体化治疗,而是关于如何从产生大量心理痛苦和创伤的结构性条件中获得集体解放。这一谱系支撑着当今社区和专业人士要求废除(针对精神病患的)监禁制度的努力,并通过同伴支持、安置屋和政治抗议等构想各种非暴力形式的治疗护理。例如,去年(2021)在洛杉矶,一个由社区组织者、学者和官员组成的联盟成功地阻止了一间 “精神病监狱” 的建设,并主张将这些资金再投入以社区为基础的精神卫生保健计划。 “治疗第一,监狱最后”,这是他们的要求。
对更多享有特权的人群来说,也有意想不到的教训。毕竟,物质财富并不能帮助人们免受资本主义的心理伤害。倦怠和抑郁在上层中产阶级医生和医学生中很普遍。仅举一个例子:耶鲁大学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其中许多人来自特权背景)寻求心理健康服务以解决心理困扰。正如心理治疗师 Gary Greenberg 直言不讳地说,“事实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操蛋的社会,我就会失业。”
上层社会的心理痛苦不仅证明我们需要增加获得治疗的机会,无论是通过药物还是心理治疗。这种情形要求我们动员起来,改变这个病态的社会,从有毒的培训计划和高压的大学文化再到非人性化的工厂车间。正如历史学家乔安娜·拉丁(Joanna Radin)鼓励我在药物史本科课程所讨论的,问题不仅是什么是适合我的药物?还有,如果我不需要药物,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有吗?
哈灵顿和斯卡尔当然不希望他们的书被这样解读,但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精神学科史理解为一种呼吁,在美国取消对生物精神病学的资助。拒绝一个 “革命” 或者 “复兴” 的承诺对一个研究项目来说或许无关紧要。
我们不需要成为神经科学家就可以知道心理和情感上的痛苦是 “真实的” 或 “合法的”,而且无论药物多么有效,都无法消除这个制造创伤的监狱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正如这些书告诉我们的,精神病理论的范式是多么脆弱,尽管背后生物理论的脆弱控制在最近的批评压力下终于放松了。我们职业的未来,如果有的话,并不在于有可能取得生物学突破的无力承诺。这取决于发掘和拥抱那些被忽略的精神病史和那些精神学科所关切群体其团结的谱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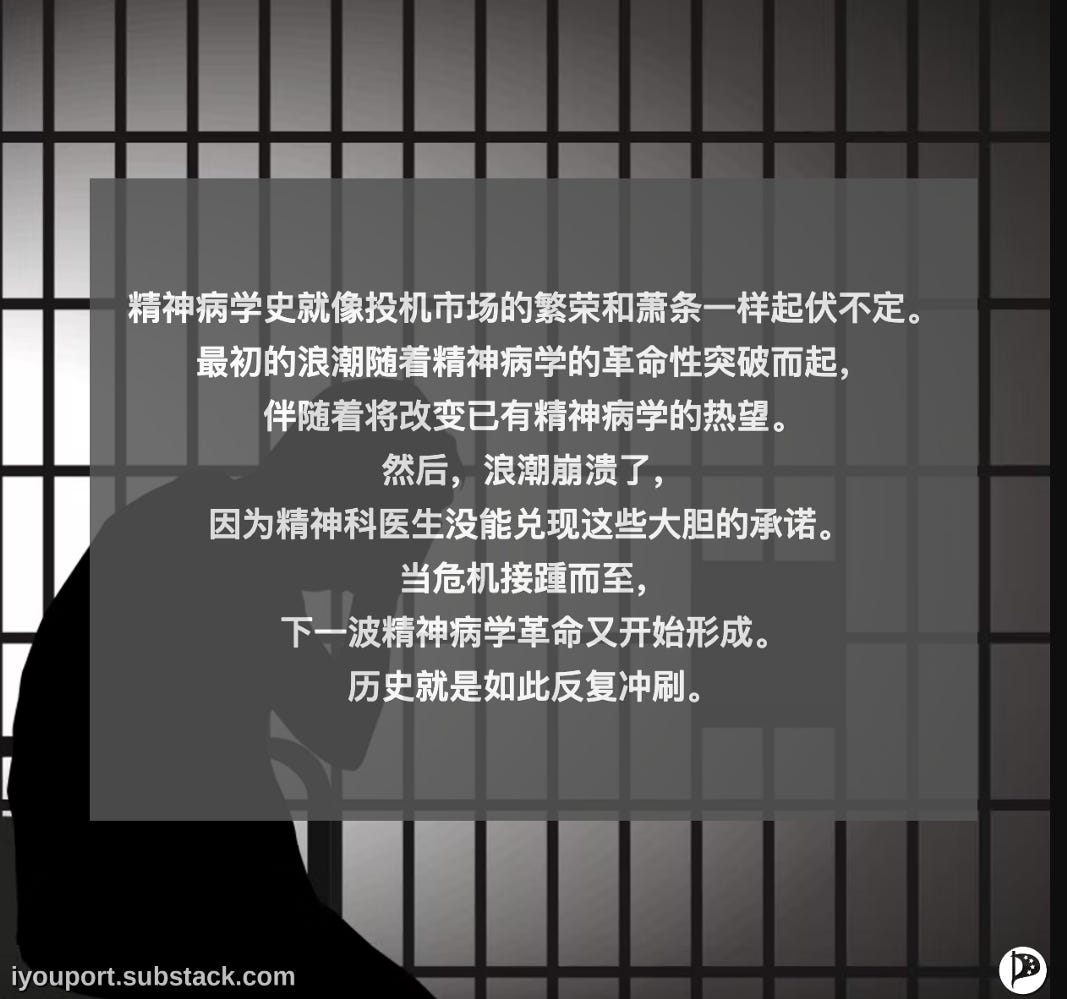











一段重抑郁
症患者的话: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我是多麼常把「我的醫師如何如何」掛在嘴邊
「我的醫師胖了」「我的醫師戴新手錶」
世界上沒有比我對我的醫師更濃烈的孺慕之情了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
我的命是他給我的
我也一直感謝著照顧我的護理師們
而關於藥物
這在其他文章裡討論過很多次
我完全信任藥物
有人說靠"勇氣" 靠"意志力" 靠"陪伴" 靠"愛"
我都不以為然
我是徹底依賴藥物康復的
一點"自我戰勝"的成分也沒有
我非常感激精神醫學,希望這點不要被誤會
现在的所谓精神疾病治疗,都是让你成为他们想要的“正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