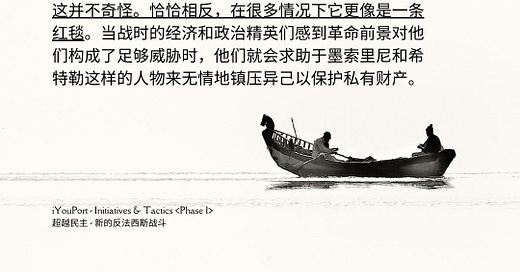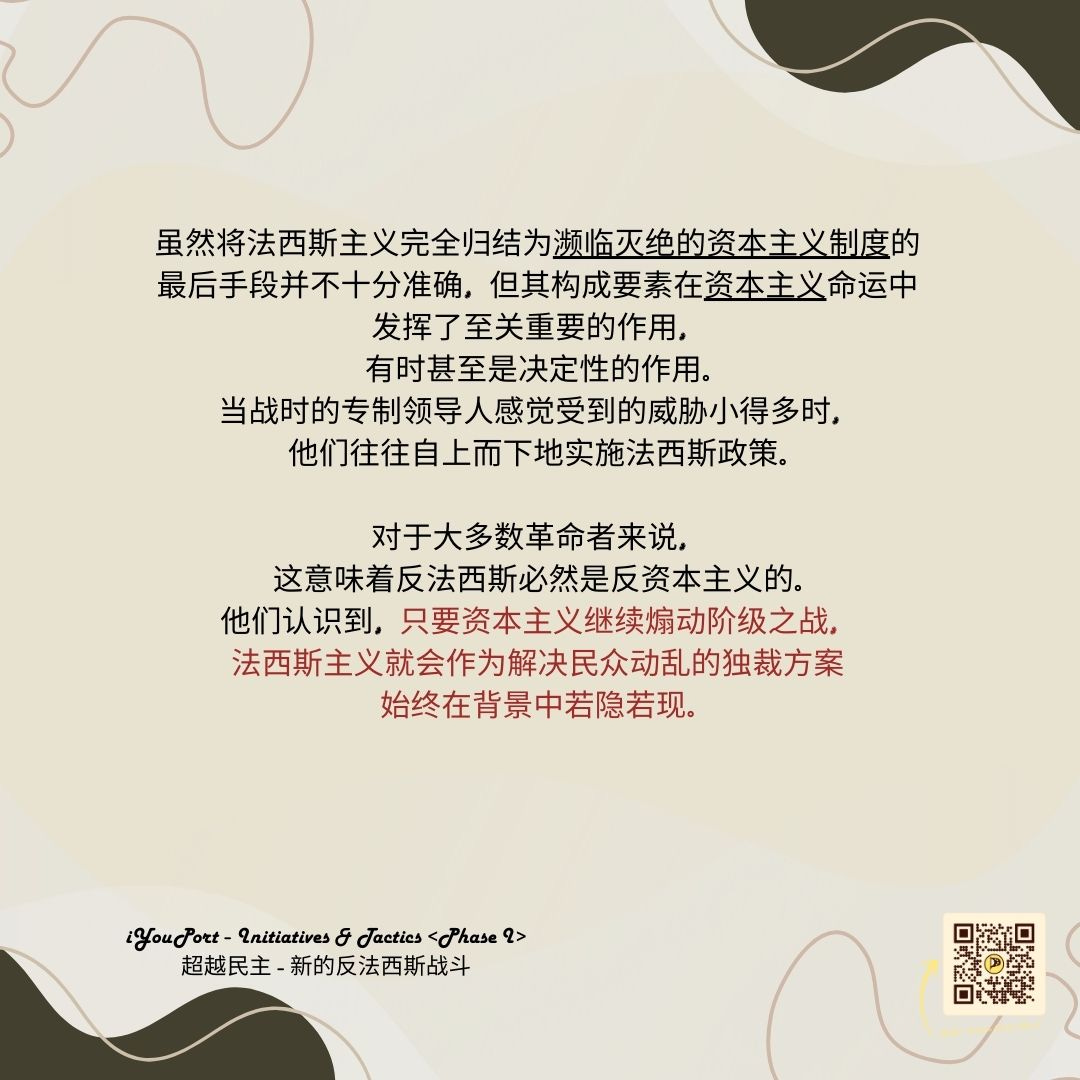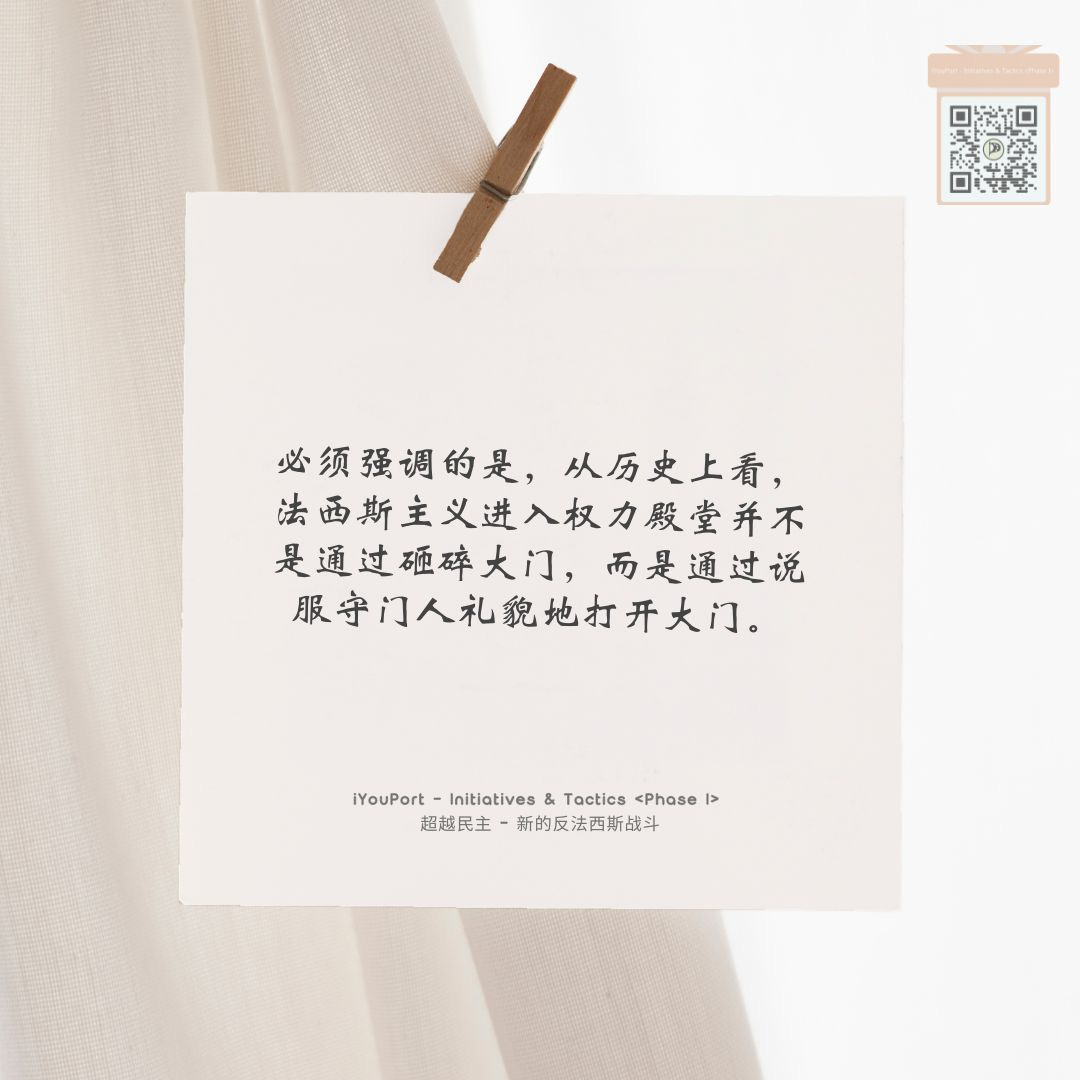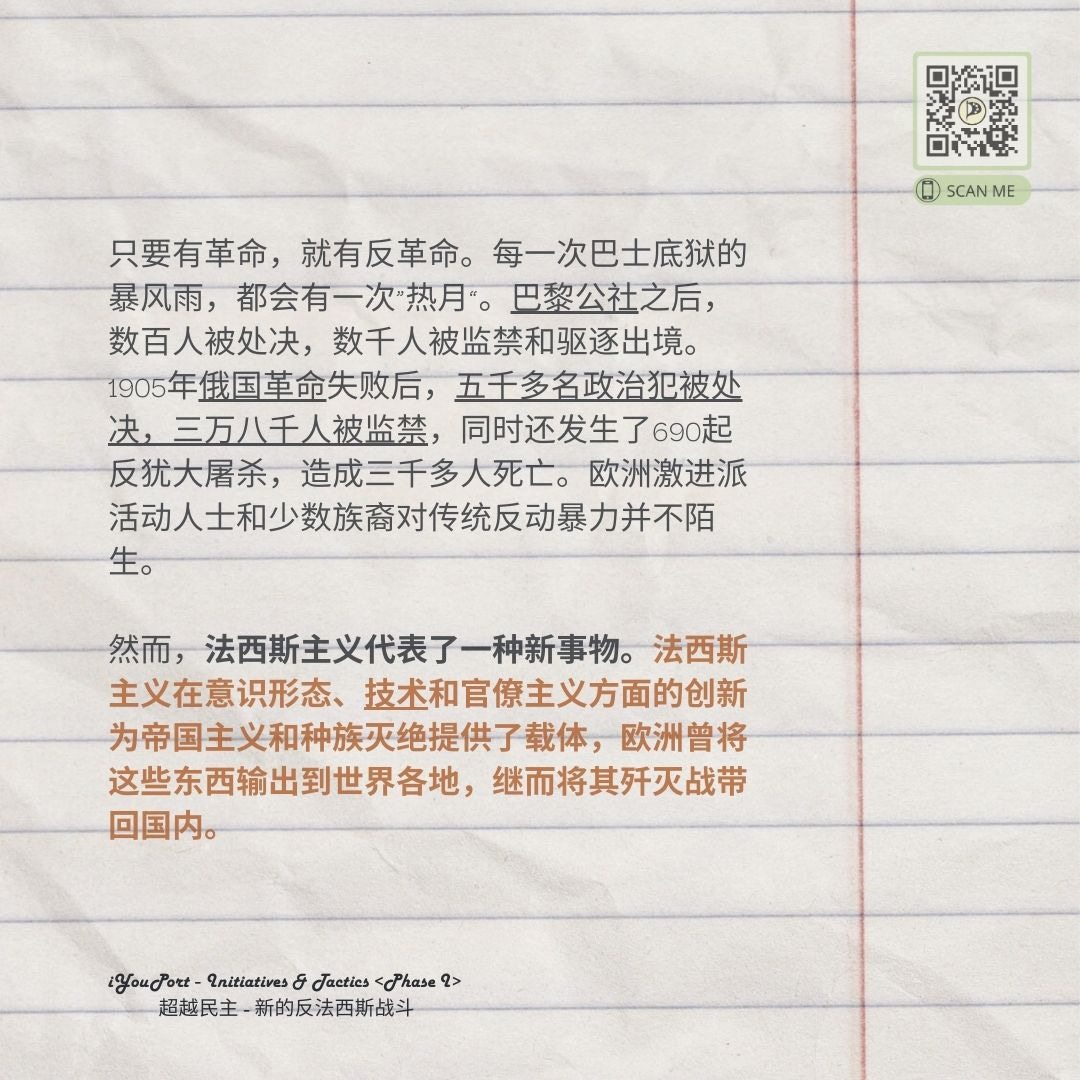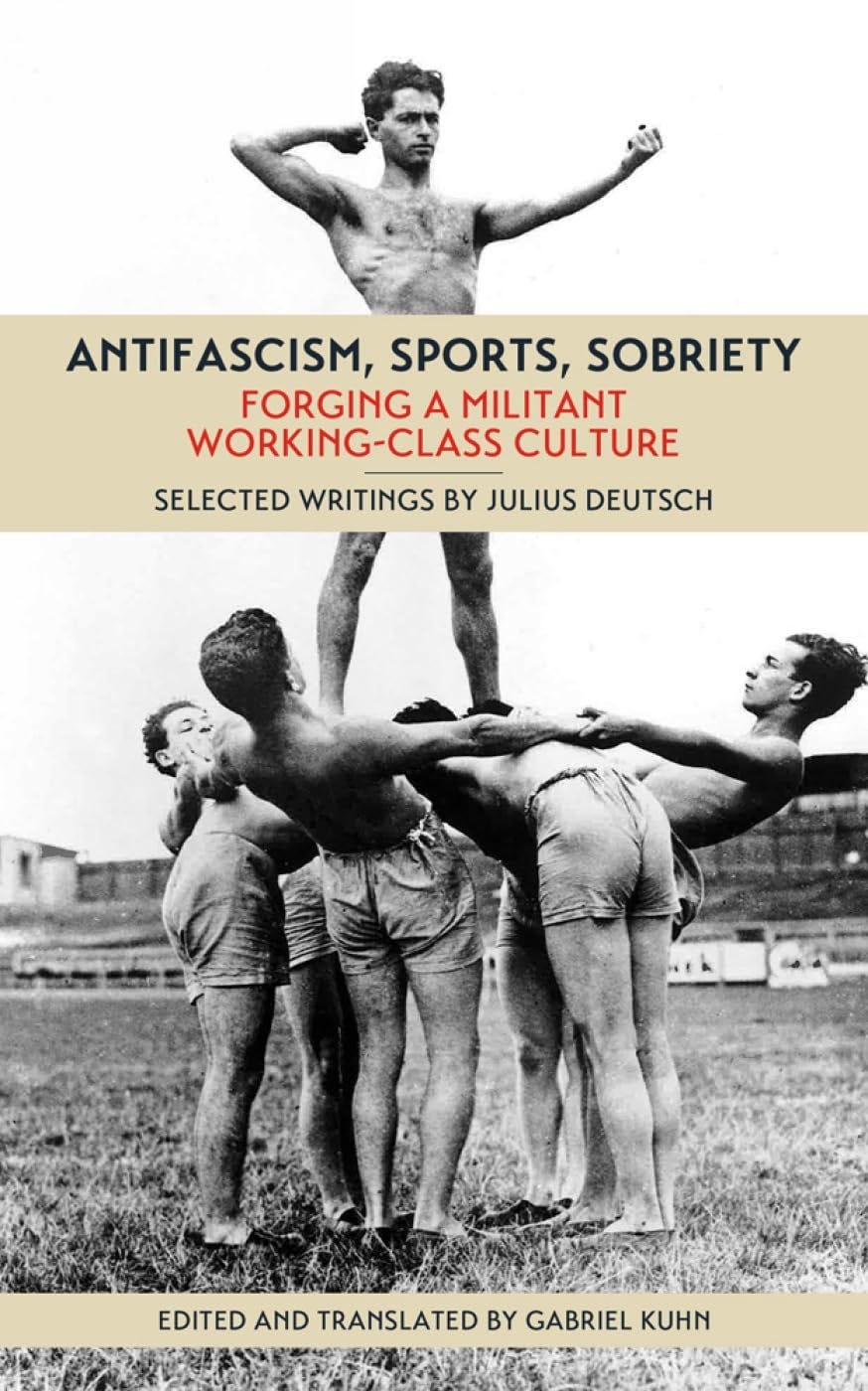反法西斯的五个历史教训
所谓的不稳定阶级是最原子化的阶级 ……"不稳定阶级内部自相残杀。其中一部分人可能会指责另一部分人的脆弱和不值得的生活方式(例如,临时工反感下层服务阶级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底层阶级内部的矛盾使人们相互对立,使他们难以意识到社会和经济结构本身才是造成他们苦难的原因。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民粹主义政客和新法西斯主义呼吁所吸引,我们已经看到这一过程在欧洲、美国和其他地方展开 ……” —— 盖伊·斯坦丁
本文和其他相关资料在近期的反法西斯社区新成员学习组中采用,现分享給所有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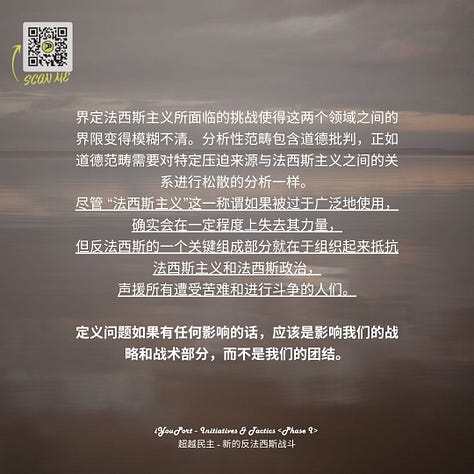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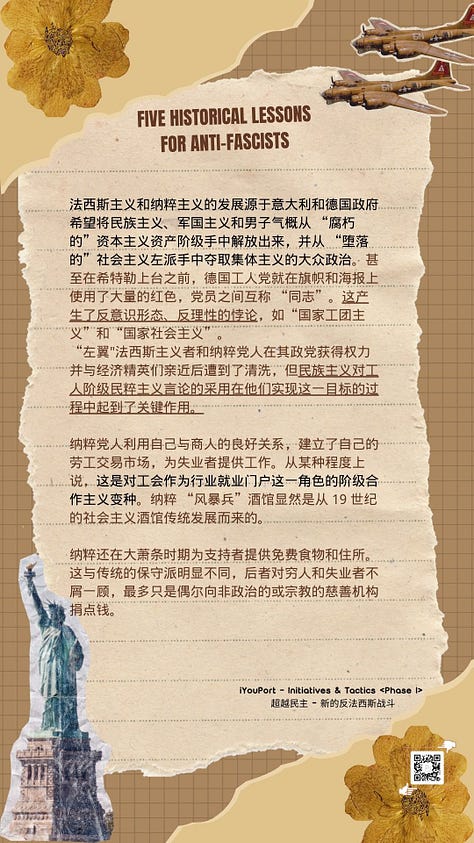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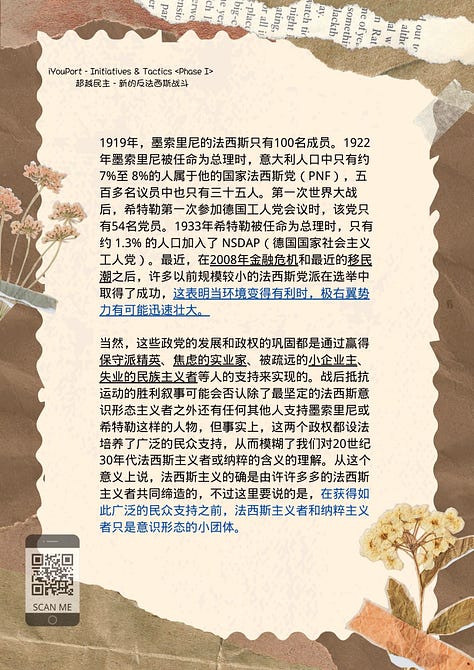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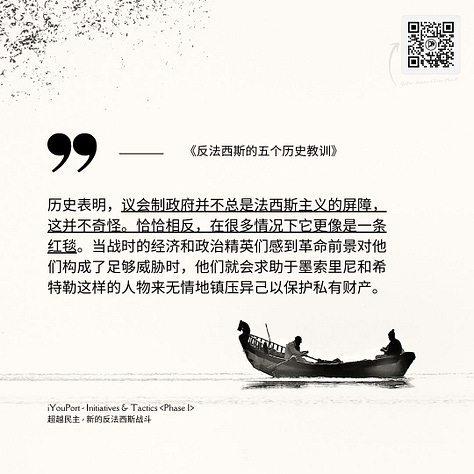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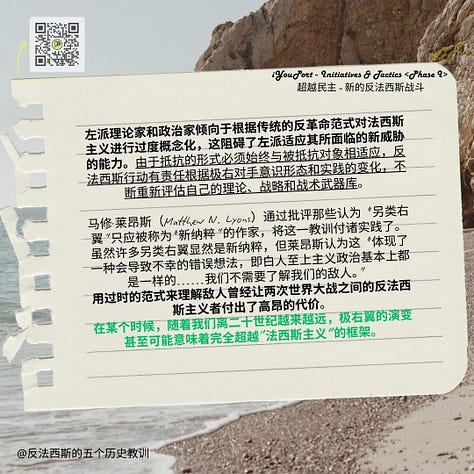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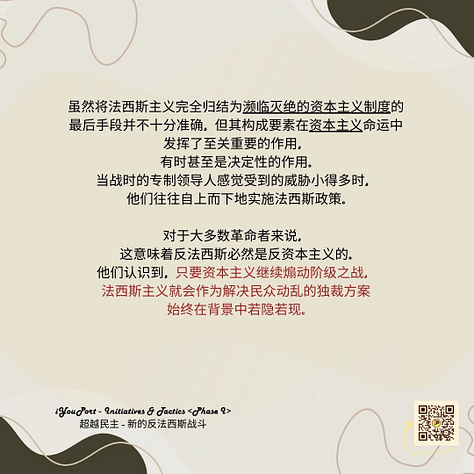
🧬 原文: 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Phase I> 超越民主 - 《反法西斯的五个历史教训》
本文简要分析了许多反法西斯人士从历史中汲取的、或者被认为应该汲取的五条主要教训。每一个教训都从对特定现象的事实描述开始,然后进入反法西斯对相关历史事实的解读。与所有历史现象一样,这些事实可以有多种解释。本文并不声称是这段历史的“全部”教训,但它们揭示了反法西斯运动的一些历史基础。
1. 法西斯革命从未成功。法西斯分子是合法掌权的。
首先是一些重要事实: 墨索里尼进军罗马不过是将其之前已经存在的政府邀请合法化。希特勒1923年的啤酒馆政变惨遭失败。兴登堡总统任命他为总理后,他才最终掌权。议会通过了授予他全部权力的《授权法案》。
对于激进的反法西斯活动家来说,这些历史事实让他们对自由派左翼的反法西斯方案产生了合理的怀疑。该方案的基本内容是:相信理性辩论能够抵制法西斯思想,相信警察能够抵制法西斯暴力,相信议会政府机构能够抵制法西斯夺权的企图。毫无疑问,这一方案有时候也许有点儿用,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其他很多时候它都毫无作用。
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是以情感化的、反理性的诉求出现的,其基础是关于重振民族活力的男性式承诺。虽然政治论证对于吸引法西斯主义潜在的群众基础始终很重要,但在面对拒绝理性辩论条件的意识形态时,其锋芒就会被削弱。理性并没有阻止法西斯或纳粹。虽然理性总是必要的,但遗憾的是,从反法西斯的角度来看,理性本身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历史表明,议会制政府并不总是法西斯主义的屏障,这并不奇怪。恰恰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它更像是一条红毯。当战时的经济和政治精英们感到革命前景对他们构成了足够的威胁时,他们就会求助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样的人物来无情地镇压异己以保护私有财产。
虽然将法西斯主义完全归结为濒临灭绝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手段并不十分准确,但其构成要素在资本主义命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当战时的专制领导人感觉受到的威胁小得多时,他们往往自上而下地实施法西斯政策。对于大多数革命者来说,这意味着反法西斯必然是反资本主义的。他们认识到,只要资本主义继续煽动阶级之战,法西斯主义就会作为解决民众动乱的独裁方案始终在背景中若隐若现。
至于对“警察抵制法西斯暴力”的想法 —— 有些时候警察的确可以逮捕和压制法西斯分子,但是历史记录显示,警察与军队一样,也是最渴望 “恢复秩序” 的人群之一。研究表明,在过去多年中,投票支持 “金色黎明”和 “国民阵线”的警察比例很高。 在美国,许多警察显然欢迎特朗普成为 “Blue Lives Matter” 总统,允许执法部门继续不受阻碍地骚扰和谋杀有色人种。最近有消息称,联邦调查局几十年来一直在调查白人至上主义对执法部门的高度渗透,这令人惊讶(尽管并不意外)。此外,无论美国警察队伍的构成如何,它从南方奴隶巡逻队和北方镇压劳工运动发展而来这一事实,足够让人们对其在白人至上主义刑事 “司法”系统中的作用有了深入了解。
综上所述,法西斯起义总是以失败告终,但这并不能减少人们对法西斯起义的担忧。意大利法西斯的 “紧张战略”、美国三K党领袖路易斯·比姆(Louis Beam)提倡的 “无领导抵抗”的独狼概念的发展,以及乌克兰Maidan起义双方发展起来的法西斯武装斗争,都证明了法西斯暴力叛乱的实质危险。
必须强调的是,从历史上看,法西斯主义进入权力殿堂并不是通过砸碎大门,而是通过说服守门人礼貌地打开大门。
2. 许多战时反法西斯领导人和理论家在不同程度上认为法西斯主义只是传统反革命政治的变种。他们没有足够重视这一点,直到为时已晚。
只要有革命,就有反革命。每一次巴士底狱的暴风雨,都会有一次“热月”。巴黎公社之后,数百人被处决,数千人被监禁和驱逐出境。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五千多名政治犯被处决,三万八千人被监禁,同时还发生了690起反犹大屠杀,造成三千多人死亡。欧洲激进派活动人士和少数族裔对传统反动暴力并不陌生。
然而,法西斯主义代表了一种新事物。法西斯主义在意识形态、技术和官僚主义方面的创新为帝国主义和种族灭绝提供了载体,欧洲曾将这些东西输出到世界各地,继而将其歼灭战带回国内。
毫不奇怪,许多左翼评论家最初将法西斯主义概念化为现有的反革命力量。根据工人社会主义联盟的说法,意大利法西斯分子 “在严格意义上是白军”,指的是俄国革命中的反革命分子;英国共产党称他们为 “意大利版的黑棕部队”,指的是爱尔兰独立战争中英国的反革命势力。20世纪20年代,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利用匈牙利共产党人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acs)对 “白色恐怖”的分析,认为墨索里尼的中队只是统治阶级的非意识形态堡垒。
另一方面,一些评论家确实强调了法西斯主义的独特之处。他们承认法西斯的民族主义调戏了社会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精英主义的新颖性。他们观察到,传统地主和资产阶级资本家等以往对立的阶层如何能够形成一个联合的反革命运动。马克思主义关注法西斯主义潜在的阶级动力,揭示了这一令人费解的新理论中中间派观察家未能把握的一些要素。然而,这种关注也倾向于将法西斯主义可能造成的潜在危险限制在了其作为统治阶级保镖的所谓角色范围内,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和许多其他人未能预见到法西斯主义的暴力范围将如何大大超出保护资本主义企业的 “必要”范围。此外,尽管战时法西斯主义主要是在上层阶级的支持下从中产阶级选民中发展起来的,但随着法西斯运动的发展,它们有时会吸引工人阶级的支持,尽管并非总是如此 —— 马克思主义者迟迟未能完全接受这一事实。
然而,无论他们的分析内容如何,许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家在领导时并没有把他们运动的存亡视为岌岌可危。意大利社会主义者于1921年与墨索里尼签署了《绥靖条约》,他们和共产党人都认为墨索里尼的上台“只是”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古老而有节奏的钟摆中“最新的一次右摆而已”。在这方面,他们和20世纪20年代与普里莫·德里维拉(Primo de Rivera)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军政府合作的大多数西班牙社会主义者并无二致。在德国,当20世纪30年代初的 “总统政府” 开始通过法令进行统治时,共产党人认为法西斯主义已经到来。然而,无论是所谓的法西斯 “总统政府”,还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总理职位,都没有让党的领导层相信他们已经面临着生存威胁。对于德共领导层来说,他们认为法西斯主义并不需要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抵抗,而是要求耐心等待。他们的口号是 “先希特勒,后我们”。在世纪之交,左派应该也必需能预见到,镇压的时代会来来去去。法西斯主义已经改变了游戏规则。
1934年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发动 “二月起义”,反抗专制总理陶尔斐斯(Dollfuss)对社会主义中心的袭击(由墨索里尼策动)。这是人们对法西斯危险本质的第一次实质性认识。起义遭到残酷镇压,造成200人死亡,300人受伤,该党被取缔。然而,他们的“英勇事迹”鼓舞了西班牙的社会主义矿工,他们于当年晚些时候在阿斯图里亚斯发动了起义。他们的口号是 “维也纳比柏林好”,在那里,希特勒的上台没有遭到武力的反对。到西班牙内战爆发时,人们普遍认为反法西斯是一场反抗灭绝的绝望斗争。
左派理论家和政治家倾向于根据传统的反革命范式对法西斯主义进行过度概念化,这阻碍了左派适应其所面临的新威胁的能力。由于抵抗的形式必须始终与被抵抗对象相适应,反法西斯行动有责任根据极右对手意识形态和实践的变化,不断重新评估自己的理论、战略和战术武器库。马修·莱昂斯(Matthew N. Lyons)通过批评那些认为 “另类右翼”只应被称为“新纳粹”的作家,将这一教训付诸实践了。虽然许多另类右翼显然是新纳粹,但莱昂斯认为这 “体现了一种会导致不幸的错误想法,即白人至上主义政治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不需要了解我们的敌人。” 用过时的范式来理解敌人曾经让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某个时候,随着我们离二十世纪越来越远,极右翼的演变甚至可能意味着完全超越“法西斯主义”的框架。
🧬 原文: 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Phase I> 超越民主 - 《反法西斯的五个历史教训》
反法西斯活动家必须对法西斯主义有清晰准确的认识。然而,为了理解反法西斯政治的稳健性和灵活性,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反法西斯行动众多范畴中的两个主要范畴之间的关系:分析范畴和道德范畴。
分析范畴包括调动有历史依据的法西斯主义定义和解释,以制定适合应对意识形态法西斯团体和运动的具体挑战的反法西斯战略。对抗新纳粹团体的方法可能对其他极右翼组织没有意义。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应有助于战略和战术的选择。
道德范畴是从战后时期“法西斯”这一称谓的修辞力量中发展起来的 —— 将某人或某物称为“法西斯”。当反法西斯的视角被应用于从技术上讲可能不是法西斯、但却是法西斯主义的现象时,它就会开始发挥作用。
例如,黑豹党称肆无忌惮杀害黑人的警察为 “法西斯猪”,如果这些警察个人角度上并不持有法西斯信仰,或者美国政府并非真正的法西斯政府,那么黑豹的描述是否错误呢?在马德里的一次反法西斯示威中出现了一面彩虹旗,上面写着 “仇视同性恋就是法西斯主义” 的标语。非法西斯的纯恐同者的存在是否会使这一论点失效?如果根据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观点,西班牙的佛朗哥或智利的皮诺切特政权在技术层面上并不是法西斯,那么反对这些政权的游击队称他们的斗争为 “反法西斯” 是否有误?
正如我们所讨论的那样,对这些案例以及其他更多案例进行逐一的和精细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反法西斯的道德准则理解了 “法西斯主义” 是如何成为一种道德符号的,那些与各种压迫作斗争的人们利用这种符号来强调他们所面对的政治敌人的凶残,以及它们与真正的法西斯主义所共有的连续性因素。与法西斯主义本身相比,佛朗哥的西班牙可能更像是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军事政权,但对于那些被国民卫队追捕的人来说,这种差异并不重要。
界定法西斯主义所面临的挑战使得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分析性范畴包含道德批判,正如道德范畴需要对特定压迫来源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松散的分析一样。尽管 “法西斯主义”这一称谓如果被过于广泛地使用,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其力量,但反法西斯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就在于组织起来抵抗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政治,声援所有遭受苦难和进行斗争的人们。
定义问题如果有任何影响的话,应该是影响我们的战略和战术部分,
而不是我们的团结。
3. 由于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原因,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领导层在准确评估法西斯主义威胁方面往往慢于其党内普通成员,在倡导激烈的反法西斯对策方面也慢于其党内普通成员。
由于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起初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传统反革命政治的变种,因此他们对彼此的关注远远超过对法西斯敌人的关注。两派都[错误地]认为,只要能将无产阶级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下,那么他们可能面临的右翼障碍也就不重要了。
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初,当一些普通的社会主义者留在反法西斯组织‘人民阿迪蒂突击队’与意大利的黑衫军作战时,党的领导层却退出了,以便继续沿着其法律化的选举道路前进。当这条道路被彻底堵死时,该党又奋力改弦更张。
整个时期都是如此: 德国社会主义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坚持严格的法律路线,尽管党员们越来越感到不安。尽管黑红金国旗团(Reichsbanner)和后来的钢铁阵线(Iron Front)中的社会主义者都在推动采取更激进的措施,但迟钝的党机构却没有能力考虑其他战略。同样,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面对极右翼分子的猛烈进攻,奥地利社会主义的普通党员也竭力推动党的领导层采取激进的自卫行动。在英国,工党和工会大会的普通党员不顾领导人的劝诫,在街头与法西斯分子直接肉搏。工党领导层甚至谴责参加凯布尔街战役的工党成员(当时多个团体在伦敦东区犹太人聚集区与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的黑衫军对峙),领导层还拒绝支持许多加入西班牙的国际纵队的工党成员。正如历史学家拉里·塞普莱尔(Larry Ceplair)所言,社会民主党人 “玩议会游戏玩得太久了,[他们的]领导人在意识形态和心理上都已经无法组织、命令或批准武装抵抗或预防性革命”。
尽管如此,许多社会主义者个人似乎对当地不断变化的情况更加敏感,也更加渴望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他们远没有受到法治主义政党意识形态和选举策略总体规划的束缚。
20世纪20年代初,共产国际认为,革命的当务之急是明确区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界限,这样他们才能领导似乎已经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的起义浪潮。随着1928年共产国际 “第三阶段”的开始,这一目标再次凸显出来。列宁主义的 “民主集中制”组织模式规定了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到国家政党再到地区支部和社区干部的纪律严明的指挥系统。这种模式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能够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统一行动,但也往往意味着莫斯科党内精英之间的内讧对政策的影响要远大于当地的实际情况。
“社会法西斯主义”路线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许多国家领导人勉强采纳了这一路线,但随着 1935 年共产国际转向人民阵线政策,他们又急切地放弃了这一路线。普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者彼此之间一般不会像他们的领导人那样相互憎恨。事实上,例如在法国和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早期团结倡议都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这些例子都能表明等级制度化的组织天然具有的弊端。
4. 法西斯主义窃取左翼意识形态、战略、形象和文化。
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发展源于意大利和德国政府希望将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男子气概从 “腐朽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手中解放出来,并从 “堕落的”社会主义左派手中夺取集体主义的大众政治。甚至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工人党就在旗帜和海报上使用了大量的红色,党员之间互称 “同志”。这产生了反意识形态、反理性的悖论,如“国家工团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左翼"法西斯主义者和纳粹党人在其政党获得权力并与经济精英们亲近后遭到了清洗,但民族主义对工人阶级民粹主义言论的采用在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纳粹党人利用自己与商人的良好关系,建立了自己的劳工交易市场,为失业者提供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工会作为行业就业门户这一角色的阶级合作主义变种。纳粹 “风暴兵”酒馆显然是从 19 世纪的社会主义酒馆传统发展而来的。
纳粹还在大萧条时期为支持者提供免费食物和住所。这与传统的保守派明显不同,后者对穷人和失业者不屑一顾,最多只是偶尔向非政治的或宗教的慈善机构捐点钱。
希腊极右政党“金色黎明”、意大利“卡萨庞德(Casapound)”、马德里 “社会之家(Hogar Social)”、和英国 “国家行动(National Action)”组织都采用了这种极右政治慈善模式,开始只向希腊裔、意大利裔、西班牙裔和 “白人”发放免费食物和日用品。“卡萨庞德”的活动分子甚至开始模仿自治主义的占屋行动,占据废弃的建筑物,而马德里极右翼“社会之家”不仅也模仿占屋活动,甚至有时还组织反对驱逐西班牙裔人的活动,显然是想利用西班牙活跃的左翼住房权利运动的影响力。
更广泛地说,战后法西斯继续向革命左翼寻求战略启示。“第三位置”法西斯分子试图将毛泽东的第三世界革命理论应用于 “欧洲解放”的目标,这就需要强行清除 “非欧洲人”。20世纪80年代,法国 “第三位置”(Troisième Voie)的一个派别试图利用“‘托洛茨基主义’战略”打入国民阵线,以便从内部接管该阵线。乌克兰法西斯分子试图利用乌克兰无政府主义领袖内斯托尔·马赫诺(Nestor Makhno)的政治遗产,而西班牙新纳粹组织“自治基地”(Bases Autónomas)则称赞无政府主义者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Buenaventura Durruti)。
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始,欧洲各地的法西斯分子甚至开始效仿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的黑群战术,但在2000年代末逐渐壮大。这些身着黑衣的 “自治民族主义者”有时甚至会使用带有国家社会主义口号的反法西斯旗帜标志,有时则佩戴巴勒斯坦卡菲耶头巾,他们试图模仿激进左派的号召力,在德国、希腊、捷克、波兰、乌克兰、英国、罗马尼亚、瑞典、保加利亚和荷兰等国倡导反资本主义、反军国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2013年前后,这一趋势在西欧开始衰退。“民族国家无政府主义”是这一主题的另一种新变体 —— 其滥用无政府主义的自治概念,主张建立独立的、同质的 ”民族飞地",包括种族主义的“白人家园”。
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但这些例子足以说明反法西斯运动不仅要大胆地反对法西斯主义,还要像亚历山大·里德·罗斯(Alexander Reid Ross)这本奇妙著作的标题所暗示的那样,防范法西斯主义的蠕变。这些例子还证明了左翼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如果不确定它们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那么 “自治”、“民族解放”甚至 “社会主义”等概念,以及寮屋行动、组织食物募捐或组建黑群等战术,都可能在我们眼皮底下被收编。
5. 形成法西斯主义并不需要很多法西斯分子。
1919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只有100名成员。1922年墨索里尼被任命为总理时,意大利人口中只有约7%至 8%的人属于他的国家法西斯党(PNF),五百多名议员中也只有三十五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希特勒第一次参加德国工人党会议时,该党只有54名党员。1933年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时,只有约 1.3% 的人口加入了 NSDAP(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最近,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最近的移民潮之后,许多以前规模较小的法西斯党派在选举中取得了成功,这表明当环境变得有利时,极右翼势力有可能迅速壮大。
当然,这些政党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都是通过赢得保守派精英、焦虑的实业家、被疏远的小企业主、失业的民族主义者等人的支持来实现的。战后抵抗运动的胜利叙事可能会否认除了最坚定的法西斯意识形态主义者之外还有任何其他人支持墨索里尼或希特勒这样的人物,但事实上,这两个政权都设法培养了广泛的民众支持,从而模糊了我们对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者或纳粹的含义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西斯主义的确是由许许多多的法西斯主义者共同缔造的,不过这里要说的是,在获得如此广泛的民众支持之前,法西斯主义者和纳粹主义者只是意识形态的小团体。
但与此同时,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当墨索里尼组建了一个由一百名愤慨的退伍军人和古怪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者组成的乌合之众,希特勒为争夺小小的德国工人党的领导权而展开激烈斗争时,意大利和德国似乎正处于社会革命的边缘。
左派不该对这两个事态发展视而不见。
鉴于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当时所了解的情况,他们没有理由在法西斯主义早期投入任何时间或注意力。然而,人们可能会好奇,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会发生什么?这是不可能认真解决的反事实问题,而且过分纠缠于此,忽略了为法西斯主义崛起奠定基础的更大的社会因素。尽管如此,反法西斯斗争还是会得出结论,既然未来是无法书写的,而法西斯主义往往产生于边缘化的小团体,那么每一个法西斯主义或白人至上主义团体都应该被当作墨索里尼的一百个法西斯、或者是为希特勒提供第一块垫脚石的德国工人党的五十四名成员。
现代反法西斯运动的悲剧性讽刺在于,它越成功,其存在的理由就越受到质疑。反法西斯的最大成功处于一个假设的边缘:在过去的七十年里,有多少凶残的法西斯运动被反法西斯组织在其暴力蔓延之前扼杀在萌芽状态?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 这的确是件非常好的事。
🏴
🧬 原文: 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Phase I> 超越民主 - 《反法西斯的五个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