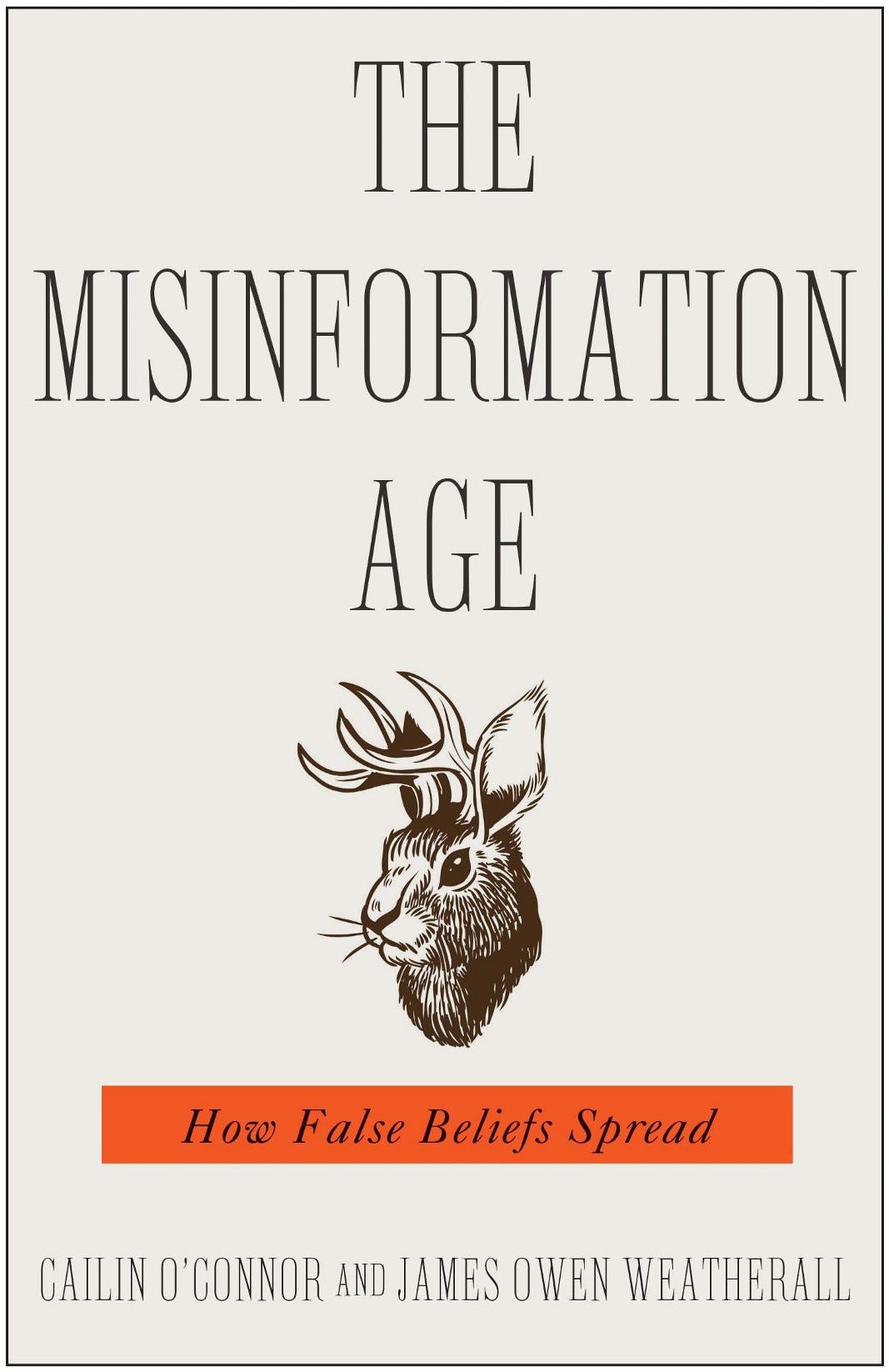【按】如果一个人告诉您西红柿炒鸡蛋需要先放西红柿后放鸡蛋,您选择信还是不信?您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您的判断标准在多大程度上和西红柿或鸡蛋有关?而不是告诉您这件事的那个人?如果告诉您这件事的那个人被证明与您的意识形态立场相悖(您是左他是右,或者您是右他是左),您还相信他的话吗? 这不是个玩笑。这件事的结果已经造成了当下的民主危机。
去年底的对话中我们强调了 “超越左右”,从真相事实开始对话,从愿景入手进入行动,而不是意识形态;这并不是什么创新,而是一种紧迫的需求。这本书需要讲述的就是这个问题。
这本书在这里下载:https://www.patreon.com/posts/zhen-xiang-de-48705422
在学术界的行话中,研究人们能知道什么、以及人们如何能知道它,被称为 “认识论”。在20世纪80年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宣布认识论终于结束了。对罗蒂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其他思想家来说,我们甚至需要一种认识论的想法,是建立在过时的、笛卡尔式的假设上的,即 心灵是自然界的一面纯真的镜子;他敦促我们把婴儿 — — “真理” — — 和十七世纪理性主义的洗澡水一起倒掉。他在其最后一本书(2007年出版)的挑衅性标题中问道:“真理有什么用?” 他的答案就像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是明确的:没太大用。
事情发生了变化。罗蒂在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和谷歌出现之前就写出了他的主要作品。即使在互联网的早期,许多人也坚持认为它能促进信息的民主化 — — 如果它能对社会有任何影响的话。随后的数十年让这种乐观情绪迅速收敛了,但也让知识问题变得更加紧迫,更加有根有据。当数以百万计的选民不顾一切证据,相信选举是被盗的、相信疫苗是危险的、相信一伙儿童色情狂在披萨店的地下室里统治世界时,显然已经不能忽视知识是如何形成和被扭曲的。当下正在经历的是一场认识论危机。
因此,认识论不仅准备再次成为 “第一哲学”。在真正的意义上,我们现在都必须成为认识论者 — — 特别是一种应对政治世界挑战的认识论,一种政治认识论。
对知识如何在社会群体中获得和分配的兴趣,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科学的实质性研究领域。但除了显着的例外— —如WEB杜波依斯、约翰·杜威、托马斯·库恩和米歇尔·福柯— —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大多关注个体:他们的核心关注点是“我如何知道”,而不是“我们如何知道”。但这种情况在世纪末开始发生变化,因为琳达·阿尔科夫等女权主义理论家和查尔斯·米尔斯等黑人哲学家不仅呼吁人们关注知识的社会层面,而且要关注它的反面— —无知。此外,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这些传统研究,以阿尔文·戈德曼为首的分析哲学家发起了对证言(“我们何时应该相信别人告诉我们的东西”)、群体认知、以及同行和专家之间的分歧等问题的探究。
总的结果是,哲学上的关注点转移到了一群人如何决定他们知道的问题上。毫不奇怪,这种关注现在越来越多地集中在数字和政治如何交织在一起以改变人们生产和消费信息的方式上。这种兴趣在 Cailin O’Conner 和 James Weatherall 最近出版的《错误信息时代:错误的信念是如何传播的》(2019)一书中,以及 C. Thi Nguyen 关于回音室(成员主动不信任 “外部” 来源)和认识论泡沫(成员只是缺乏相关信息)之间的区别的研究得到了展示。这些例子凸显了哲学如何能够为当下最紧迫的文化问题做出贡献,即:我们如何相信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
贯穿这项工作的一个显着的主题是,我们可以研究知识的社会基础,而不必放弃客观性和真理等概念,即使必须重新想象我们如何获得和实现这些价值。而在许多人认为民主中的真理价值受到威胁的时候,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为了理解这意味着什么,思考一下人们需要政治认识论来帮助解决的一些问题 — — 可以称之为对民主的认识论威胁 — — 会很有帮助。民主政体特别容易受到这种威胁的影响,因为在需要公民的商议参与时,人们必须特别重视真相。
并不是说像一些保守派每当进步人士谈论真相时似乎认为的那样,认为民主政体应该试图让每个人都相信同样的东西 — —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民主了。相反,民主政体必须特别重视那些帮助人们可靠地追求真相的制度和实践 — — 获得知识而不是谎言,获得事实而不是宣传。对民主的认识论威胁就是对这种价值和这些制度的威胁。
事实上,当前政治格局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人们不仅在价值观上有分歧(这在民主制度中是健康的),也不仅在事实上有分歧(这是不可避免的),最致命的是,在人们确定 “什么是事实” 的标准上也有分歧。把这叫做知识两极化,或者说是关于谁能 “知道” 的分歧 — — 应该相信哪些专家、以及什么是理性的,什么不是。
人们对 COVID-19 疫情的反应是这种两极分化危险的痛苦例证。在流行病开始的早期,甚至在全国感染率飙升的时候,Knight/Gallup 的民调显示,一个人的政治观点,以及他们的新信息来源,预示着他们对公共健康风险的严重程度。共和党人更有可能相信病毒的致命性被夸大了。正如一位推特用户所说,“对不起,自由派,但我们不相信安东尼·福齐博士” 。
关于 “认识论溢出效应” 的研究表明了知识两极分化的政治化程度到底有多深。当政治信念影响了人们愿意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某人在一项与政治无关的任务上的专业知识时,就会发生认识论溢出。
在一项探讨日常生活中这种情况如何发生的研究中,参与者既能了解其他参与者的政治取向,也能了解他们在一项完全无关的、非政治性任务(通常是极其基本的,如形状分类任务)中的能力。然后,参与者被问及他们会咨询谁来帮助他们自己完成任务。结果是:人们更愿意相信同一政治部落的人,即使是识别形状这样平庸的事。而且,即使他们有证据表明他们的政治同族在这项任务上更差,即使有经济上的激励来遵循这些证据,他们也会继续这样做。
换一种说法,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更容易相信民主党的医生、民主党的水管工、和民主党的会计师 — — 即使他们有证据表明这将导致更糟糕的结果。
类似的研究都足够表明,意识形态政治和知识两极分化在不信任的反馈循环中相互补充。如果你认为民主党人是被洗脑的自由派媒体的奴隶,那么当他们告诉你有疫情出现、或者地球变暖、或者选举是公平的时候,你就不会相信他们所谓的专业知识。事实上,政治光谱两边的不信任都鼓励了相互的怀疑 — — 正是认识论者经常被指责花太多时间担心的事。
这种怀疑主义会阻碍人们按照证据得出能救命的结论 — — 从而拒绝戴上口罩或保持社交上的距离。而且,至少在两个方面,它还会威胁到一个社会对保护和公平分配准确信息的承诺。
首先,当人们出于政治原因而不信任机构的专业知识时 — — 不管是关于疫苗的还是气候变化的,他们就不会重视这种专业知识指导下的研究。而这反过来又削弱了寻求真相的民主价值 — — 例如,资助联邦研究机构 — — 尽管它有很多不足之处,但它的目的是帮助人们弄清应该相信什么和如何行动,包括在投票箱中。
其次,怀疑的不信任也会奇怪地让人们挖空心思。古希腊的皮浪主义者认为怀疑主义是健康的,因为它会让人变得更加 … 嗯,怀疑 — — 也就是说,不太可能相信愚蠢的东西。但人类的悲惨历史表明,他们太乐观了:知识的两极分化似乎使人们对自己的观点有更多的信心,而不是更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种可能是人的心理弱点 — — 特定的思想态度 — — 被镶嵌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中。而也许没有什么态度比知识分子的傲慢更有毒害性了,这种社会心理态度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向别人学习的,因为你已经知道了一切了。网络上流行的一个版本是达克效应(Dunning-Kruger effect),它提出知识有限的人更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 — — 他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哲学家亚历山德拉·塔内西尼在她即将出版的《自我的错误测量》一书中认为,这种傲慢不仅仅是错位的过度自信,也是真相与自我的混淆。
傲慢是个坏消息,无论从个人来说还是心理上来说,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十六世纪的哲学家米歇尔·德·蒙田深信,傲慢会导致武断的极端主义,并可能导致政治暴力。教条主义的热情对仇恨有奇效,但从未把人拉向善良。他有句名言,“没什么比人更可怜也更自大的了”。
但真正的政治问题不是傲慢的个人本身,而是傲慢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是围绕着 “我们” 知道(秘密的真相、现实的真实本质)而 “他们” 不知道的核心信念建立起来的。对那些被这种意识形态所控制的人来说,反驳的证据被认为是对 “我们是谁” 的生存威胁。换句话说,傲慢的意识形态使一个人对证据的修正能力具有免疫力;它鼓励其追随者采取何塞·梅迪纳所说的 “主动的无知”。
傲慢会产生授权,而授权又会滋生怨恨 — — 形成极端主义的有毒心理土壤。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很容易被鼓励。正如塔内西尼所强调的那样,傲慢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不安全感的基础上,建立在对真实的或想象出的威胁的恐惧上,无论是来自崇拜撒旦的儿童色情狂还是来自外太空的犹太激光。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对民主的最明显的认识论威胁上,这种威胁滋生了其他的威胁,也被其他的威胁所滋生:阴谋论、以及历史学家蒂莫西·D·斯奈德所说的大谎言。人们经常争论那些说和分享某种东西的人是否 “真的” 相信它们,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认可它们是一种党派身份的表达。但这可能是一个完全错误的问题。
稍微换个角度,我们真正需要了解的是,大的政治谎言是如何变成信念的。信念不仅仅是一个人 “深深相信” 的东西(我相信二加二等于四,但那不是信念);信念是一种反映身份的承诺。它体现了你渴望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渴望成为什么样的群体中的一员。
信念能激励人,也能激起人的热情。它们构成了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政治现实形象。而正如哲学家夸西姆·卡萨姆和杰森·斯坦利所认为的,对大谎言的一个基本见解是,它们作为政治宣传的功能,作为宣传特定世界观的方式。这就是它们的政治危害:它们激励极端主义行动并使之合理化。
但大谎言也有其他作用:它们消解了真相的价值和追求真相的民主价值。
为了理解这一点是如何运作的,想象一下,在一场足球比赛中,一名球员把球踢进了看台,但面对现实和即时回放录像,他宣称自己还是得分了。如果他坚持这样做,通常会被忽视,甚至被罚下。但如果他 — — 或者他的团队 — — 拥有足够大的权力(也许他拥有整个球场),那么他可能会迫使比赛继续,就像他的谎言是真的一样。如果比赛继续进行,那么他的谎言就成功了 — — 即使大多数人(甚至他自己的球迷)并不 “真的” 相信他没越界。这是因为谎言的作用不仅仅是欺骗,而是表明权力比真相更重要。这是个教训,如果比赛继续下去,谁也不会忘记。他已经向双方表明,规则不再真正重要,因为说谎者已经让人们把谎言当成了真相。
这就是大谎言和阴谋对民主的认识论威胁。它们积极地破坏了人们遵守一套共同的 “认识论规则” 的意愿 — — 关于什么是证据,什么不是。这就是为什么要对它们作出回应的原因:人们越是逃避它们,知识两极化和有毒的傲慢之火就会被浇上更多的汽油。
那些从事政治认识论工作的人 — — 包括那些为一本关于这一主题的学术性新 “手册” 撰稿的人 — — 可以帮助人们掌握这些威胁;并且,他们也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如何与这些威胁作斗争。
一个正在进行的争论涉及到对大谎言和阴谋论的事实核查是否有帮助。有些人引用所谓的 “逆火效应”(Backfire effect),声称辟谣实际上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会使那些被谎言控制的人更加深入其中)。最近的研究表明,幸运的是这种效应被夸大了。但仍值得澄清 “帮助” 在这里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于那些被傲慢的意识形态所控制,坚信只有自己知道而其他人都是白痴的人来说,充其量只是向他们抛出更多的事实是不会有任何帮助的 — — 如果这里所说的 “帮助” 是指 “改变他们的想法” 的话。对于这一点必须明确: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不是改变他们的想法,而是让他们远离权力的控制感。
但这是短期游戏。我们还必须关注长期游戏。幸运的是,正如芬兰人一直在表明的那样,数字扫盲如果从小开始,就会得到回报。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知识是如何在互联网上被消费、传播和破坏的;但有一点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网络信息的高度个性化正在助长知识的两极化。人们在网上遇到的几乎所有东西 — — 从 Facebook 上的新闻到最喜欢的新闻网站上的广告 — — 都是根据每个人的喜好定制的,即 定制人。而这意味着,让人们找到想看的东西变得如此光鲜简单的算法,也让人们极不可能随随便便就能遇到任何东西,除了那些自己已经容易相信的 “事实”。把这一点教给年幼的孩子们 — — 让他们去思考阴谋论和批判性思维之间的区别 — — 应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用卡萨姆的话来说,我们能做的另一件事就是 “揪出” 谎言和阴谋的政治毒药。这样做是很重要的,并不是因为这样做可以说服骗子,而是因为这样做可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 — — 包括民主制度中真相的价值。
这就是事实和证据的意义:它们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它们能帮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真实的世界,而是因为它们具有基本的民主功能。认识论规则是民主游戏之所以成为民主游戏的一部分,在这个空间里,人们不是用枪而是用理性的交流来解决问题。
当然,这些建议不是说起来那么容易的。已经不能满足于按照自己一直使用的旧的认识论规则来玩。一方面,人们接受信息方式的技术变化显然需要改变评价证据的方式;但另一方面,需要意识到我们的知识和信仰机构是如何被结构化的,以再现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傲慢意识形态。正如从桑德拉·哈丁到刘易斯·戈登等女权主义和黑人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在说的那样,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些机构也孤立和边缘化了那些具有讽刺意味的、最能看到其错误的人。因此,我们需要尊重认识论规则,是的,但也需要制定新的规则。接受这项任务就是接受政治认识论的政治部分。
也不能忽视对任何认识论事业最核心的概念多说几句的必要性。至少在硝烟散去之后,人们很容易看到,政治判断往往是错误的。从移民到医保,人们弄错的次数比弄对的次数更多。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政治上首先要讲求事实的重要性 — — 在涉及人的任何事上都要讲求真相。这种挑战的困难正是使罗蒂放弃真相在政治中无用的观念的部分原因。但当下的情况与他不同。当下已经不再有把认识论放在一边的选择。相反,我们必须重塑认识论。⚪️
真理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