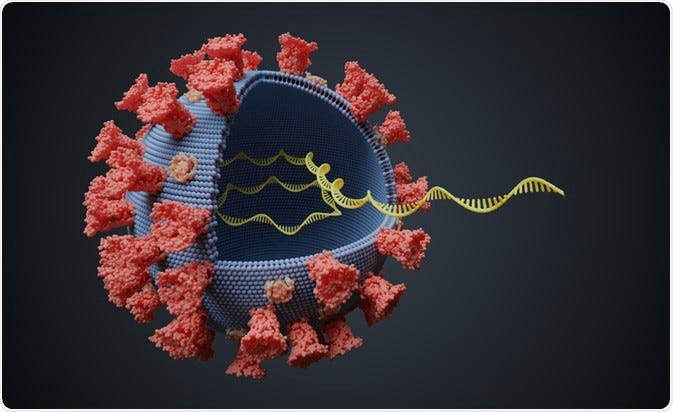"我参观了一个中国实验室。我学到的东西有助于解释关于 Covid-19 起源的冲突"
我们应该让科学和证据占上风,同时认识到,科学与其他学科一样,是由相互竞争的利益塑造的。
【注】本文不代表我们的意见。只因为IYP对流行病学一窍不通。但我们能分辨出哪些叙述是客观的,哪些带有立场的映射。我们不喜欢科学与政治利益的混淆,就如不喜欢以政治为证据推测数字技术那样。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获得健康,希望病毒传播早日终结。为了实现这点,我们需要呼吁知情人说实话。
尤其是,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知情人不愿意说实话。
本文并非流行病学论述,而是一位美国著名记者在讲述她的亲历和调查。其中关联的其他相关资源也值得您阅读。
相同主题的文章有非常之多,我们只是选了一个相对容易理解的文章给您。您信任谁或者不信任谁,完全取决于您。再一次强调,我们不做判断。
2013年,当上海出现了一种新的禽流感病毒时,我就住在上海。疫情开始于2月,农历新年后不久,一位87岁的老人和他的两个儿子因发烧和其他症状求助于当地医院。到3月初,这位老人已经死亡,导致一位匿名的中国社交媒体用户猜测围绕他死亡的奇怪情况。审查人员迅速删除了这个帖子。
上海官员最初说,该男子死于常规并发症,但是到了月底,政府的说法已经让位于一个令人不安的承认。中国卫生部通知世界卫生组织,出现了一种名为H7N9的新型禽流感病毒。死亡人数上升到7人,病例蔓延到上海周边省份。公共卫生专家失眠了,他们担心世界正处于大流行病的边缘。
与 SARS-CoV-2(导致Covid-19的冠状病毒)相比,H7N9 将变成一个小威胁,但它所走的道路对于任何在过去一年中追踪新闻的人来说都会听起来很熟悉。中国最初的病例出现之后就是审查和保密,这让人们对政府和中国科学家们的怀疑挥之不去。
我清楚地记得这一轨迹,因为在H7N9疫情爆发期间,我是《科学》杂志的首席记者。在过去的一年里,在媒体对寻找 SARS-CoV-2 起源的报道中,我多次回想我在2013年写的一篇特别报道。
我介绍了一位正在帮助当局控制H7N9传播的流行病研究人员。甚至在她成为疫情的关键人物时,她还因为对另一种禽流感病毒所做的实验而处于科学争论的中心。这项工作涉及调整病原体,以研究它们如何变得更具传染性,这种类型的研究通常被归纳为 “功能增益” 的简称。这种实验的支持者认为,更好地了解病毒如何从一个物种传播到另一个物种,可以帮助公共卫生专家抵御自然爆发。批评者担心,她的研究非但不能帮助全球健康,反而可能引发一场大流行病。
那是在功能增益工作被搅进美国政治之前,在它与对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的情绪、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以及对科学的信心混在一起之前。共和党人相信一些声势浩大的政客,他们错误地声称大流行病肯定是由实验室泄漏造成的,而民主党人相信一些声势浩大的科学家,他们也错误地保证这种事绝对不可能发生。
如果您错过了《中国与两党关系的危险》
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在2013年,功能增益研究也是政治性的,但只是在科学界。(广义的 “功能增益” 标签可适用于风险较小的研究,但批评者主要关注的是涉及使病原体以可能对人类构成风险的方式更具传播性的研究)。了解这场辩论是掌握主流媒体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突然的转变的关键,从把对实验室泄密的猜测打上阴谋论的烙印,到热情地、草率地拥抱这一说法。
2013年,当关于一种新病毒的第一个传言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开时,我正在家里照顾一个新生儿。为了报道这种新病毒,我提前休完产假回来,并很快飞到中国东北的哈尔滨市,采访中国著名的禽流感专家陈化兰。因为我的孩子还很小,所以我把孩子和我的伴侣一起带来了。
作为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的负责人,陈负责监督H7N9的动物测试工作。像之前的许多病毒一样 — — 包括埃博拉、MERS和第一次SARS — — H7N9从动物传播给人的。所谓的自然溢出往往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地区,那里的人与动物生活在一起。(这种状况是许多科学家怀疑SARS-CoV-2有自然起源的原因之一)。对于H7N9,可能的罪魁祸首是家禽市场。我想和陈谈一谈疫情爆发的早期,当时她的实验室人员争先恐后地对从鸡和鸽子身上分离出来的H7N9病毒株进行测序和分析。
但我也想问问她的其他研究。在我进行这次访问的前不久,陈和她的同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详细介绍了用豚鼠进行的大规模功能增益实验。该实验涉及将H5N1病毒的基因片段与H1N1猪病毒的基因片段互换,然后用混合病毒感染豚鼠。她的团队发现,他们可以通过调换一个基因使病毒从一种动物跃迁到另一种动物。豚鼠代表了人类。
即使中国正处于一场明显具有自然起源的疫情中,批评者担心对病原体的风险研究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疫情。但那是八年前的事了,当时关于这种研究的讨论还没有涉及地缘政治问题。
抵达哈尔滨后,我们入住了一家新古典主义风格的酒店,俯瞰斯大林公园。我的伴侣和孩子住在那里,而我则乘车前往禽流感实验室,当时该实验室位于1949年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前建造的一个庞大的建筑群中。
哈尔滨是一个落后于中国较发达城市的北方前哨,对于科学家研究高度危险的病原体的实验室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地方,但是在中国,就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关于在哪里建立这样的实验室的决定并不总是由生物安全问题驱动的。
在这种情况下,哈尔滨已经成为一个研究中心,这是偶然性和使命感的结合。中国东北是一个拥有大量牲畜的传统农业地区。几十年前,农民的需求使哈尔滨成为一个兽医研究中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兽医科学让位于一个专注于动物的实验室,该实验室被列为生物安全等级P3,或BSL-3。2018年,哈尔滨兽医研究所搬到了一个拥有BSL-4实验室的新园区,这是最高的生物安全级别。(中国的另一个BSL-4实验室在武汉病毒研究所,该研究所是SARS-CoV-2实验室泄漏假说的中心)。

陈女士说话温和,很讨人喜欢。她带我参观了大楼中不需要穿防护服和其他保护设备的部分,并询问了我的孩子。她告诉我,当她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时,中国的病毒学家甚至难以获得可供研究的菌株。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他们又面临着其他挑战。她说:“当他们得到一种病毒时,他们只是把它放在冰箱里”,她谈到了上世纪初中国的科学家们,“人们不知道如何用病毒做研究。他们可能不乐意听我这么说,但这是事实”。
陈去了美国,在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做博士后工作,师从著名的流感科学家 Kanta Subbarao。三年后,她得到了一个回到中国的职位,领导哈尔滨的实验室。陈感觉到,研究条件正在发生变化,她说中国将成为一个令人兴奋的流感研究场所。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她的预感得到了证实。中国成为了一个进行尖端实验和拥有大量拨款预算的地方。研究人员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科学家密切合作,并在顶级期刊上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传染病监测来说,需要一个全球网络来追踪新出现的疫情,这种合作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随着中国科学的国际地位上升,它也被困扰着世界其他地方科学研究的争议所困扰。
陈关于H5N1和豚鼠的论文发表于2013年5月,当时H7N9仍在中国南部蔓延。十多位研究人员参与了这项研究,其中涉及250只豚鼠、1,000只小鼠和27,000个受感染的鸡蛋。他们的目标是确定哪些变化会使H5N1病毒更有效地传播。在调换了单一基因后,他们发现受感染的动物可以通过呼吸道飞沫将病毒传给相邻笼子里的健康动物。
一场暴风雨随之而来。英国皇家学会前主席罗伯特·梅勋爵在《每日邮报》的版面上发表评论,称这项研究 “令人震惊地不负责任”。
批评声也来自中国国内。中国科学院病原微生物学和免疫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刘文军当时告诉我,当该论文发表时,“中国的科学家们相当震惊” 。“这种人造病毒可能会在中国造成一个大问题。人们真的很担心生物安全问题”。
陈说,她的所有研究都是光明正大的,而且在抗议声中,中国农业部已经派了两个人到该实验室,以确保其病毒得到适当的储存。她的团队还开发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禽类疾病疫苗。她说,她觉得这些批评是没有根据的,并补充说,May 是一位理论生态学家,不了解她的工作。
从事类似研究的病毒学家对陈的工作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和他们中的五个人谈过。其中一位对实验的设计提出了异议,但其他的人使用了 “模范” 和 “高度尊重” 这样的字眼。荷兰鹿特丹 Erasmus MC 公司的 Ron Fouchier 告诉我,他曾梦想做与陈完全相同的实验,但由于各种限制而无法做到。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我没有得到一笔能让我负担得起与13个人一起工作两年以产生一篇论文的资助,无论那篇论文会多么出色。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 Yoshihiro Kawaoka 也高度评价了陈,并告诉我她的实验室是最先进的。
但 Fouchier 和 Kawaoka 在这个问题上并非完全中立。他们曾因类似的实验而受到批评。2011年,他们所做的涉及可能通过空气传播的H5N1病毒的研究引发了全球哗然,当时在他们发表结果之前,实验的消息被泄露。2014年,包括陈、Fouchier 和 Kawaoka 在内的研究促使批评者组成了剑桥工作小组,该小组呼吁停止对可能导致大流行的病原体的研究,等待彻底审查。
剑桥工作小组的工作促使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在同年暂停了某些类型的功能增益研究。三年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取消了这项禁令,并以一个更宽松的框架取而代之。当时,人们认为病毒学家不能自律,他们的工作需要被监管。但是,在大流行之后,对于部分政治左翼来说,这种观念已经成为异端邪说。
直到最近,关于病毒可能从实验室泄漏的说法与一个人的政治信仰才产生了关系。第一批SARS病毒曾多次从实验室泄漏 — — 包括至少两次从北京的国家病毒学研究所泄漏。1977年在苏联和中国爆发的甲型H1N1流感被认为是由苏联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用活体病毒做实验造成的。一些领先的美国实验室也有重大的安全漏洞,包括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
在大流行之前,科学媒体经常报道此类风险。在2017年一篇关于武汉病毒研究所开业的文章中,《自然》杂志提出了对生物安全的担忧。在Covid-19大流行初期,《科学》杂志也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实验室泄漏的概念,并讨论了自然溢出的问题。
然后,有影响力的传染病专家和动物学家彼得·达斯扎克进入了这个战场。达斯扎克的组织 “生态健康联盟” 向武汉病毒研究所分发了美国政府的资助资金,他与那里的研究人员密切合作。他组织了一批科学家写了一份声明,发表在2020年2月的《柳叶刀》上,谴责围绕大流行病起源的 “谣言和错误信息” 的传播。该小组写道:“我们站在一起,强烈谴责暗示COVID-19没有自然起源的阴谋论”。这封信显然否定了实验室事故的合理前景,以及关于生物武器的荒诞主张,有助于压制关于这一问题的辩论。
那年春天,当特朗普在没有引用证据的情况下将大流行病归咎于武汉实验室时,讨论变得更加激烈了。
在随后的报道中,一些记者显然认为不加批判地报道研究人员的言论是他们的职责,就好像科学家是特朗普的中立陪衬。Vox在一篇驳斥实验室泄密假说的解释文章中广泛引用了达斯扎克的话。
达斯扎克最终加入了世界卫生组织和《柳叶刀》的起源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正在调查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原因。他主持了《柳叶刀》的委员会。去年秋天,担任世卫组织人类基因组编辑咨询委员会成员的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的杰米·梅茨尔写信给《柳叶刀》编辑理查德·霍顿,指出达斯扎克的利益冲突。他补充说,他尊重达斯扎克的工作,并写道:“我绝对不是说他做错了什么,只是说其中一个可能的起源故事中包括他”。
Metzl 说,《柳叶刀》的编辑没有回信。“我当时有点天真,无法想象他们会明知故犯地做出这样的决定”,他告诉我。正如 Metzl 所指出的,利益冲突并不意味着有罪。但达斯扎克的关系助长了网上的怀疑,使那些希望得到真正答案的生物安全专家感到沮丧。

在世卫组织委员会的中国之行后,Metzl 帮助领导了一个科学家小组,他们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对SARS-CoV-2的起源进行更广泛的调查。在委员会对武汉进行了有限的考察并对选择性数据进行分析之后,他们又写了一封公开信,认为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 “非常小”。
这两封信的一些签名者是法国科学家。艾克斯-马赛大学的生物信息学教授 Jacques van Helden 告诉我,围绕大流行病起源的讨论在法国没有那么两极化,他指出,特朗普在美国已经玷污了这个问题。“我怀疑这甚至可能导致美国科学界的一部分人避免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因为表达病毒来自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会被认为是对特朗普的支持”。
另一封呼吁进行透明和客观调查的公开信紧随其后,这次是来自一群知名专家。签名的人包括福瑞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的进化生物学家杰西·布鲁姆、斯坦福大学微生物学家大卫·雷尔曼、和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和微生物学家马克·利普斯奇,他在几年前成立了剑桥工作小组,推动限制功能增益的研究。
甚至世卫组织总干事泰德罗斯·阿达诺姆·盖布雷耶苏斯也说,实验室泄漏的假说 “需要进一步调查”。Vox在其解释中添加了一个说明,指出 “科学共识已经转变”。
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修正时刻以其自身的方式是危险的。仍然没有直接证据支持实验室泄漏,许多与结果无关的科学家仍然说自然起源更有可能。事实上,科学共识并没有转向实验室的起源。但是,一些既缺乏专业知识又怀有目的的学者认为,实验室泄漏导致了这场大流行病,这是很危险的。
Bari Weiss,这位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部分时间都在抨击取消文化,最近发表了对庞培奥的采访,庞培奥告诉她,证据 “指向实验室泄漏的单一方向”,尽管他补充说,“我不能为你提供证据”。
最诚实的专家只是说他们不知道。进化生物学家布鲁姆在他的研究所发表的一份问答中说:“我们并没有对一种情况比另一种情况更有可能采取主张立场。作为一名科学家,重要的是要清楚地传达出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 — — 特别是因为这是一个热门话题”。
各方都有怨言。布罗德研究所的分子生物学家 Alina Chan 主张对实验室泄漏假说进行更全面的调查,结果她被指控为种族叛徒。病毒学家安吉拉·拉斯穆森(Angela Rasmussen)是自然起源的有力支持者,她在推特上受到了恶意的骚扰。《每日邮报》最近派狗仔队到达斯扎克的家里,然后刊登了他报警的照片。中国的科学家们也受到了围攻。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和武汉病毒研究所已经从其网站上删除了一些工作人员的信息。几周前,我收到了某人的仇恨邮件,他对我去年春天在一篇关于病毒起源的文章中提到实验室泄密的假说感到不满,当时对进步媒体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触及的,但却没有给特朗普适当的 “荣誉”。
我们应该让科学和证据占上风,同时认识到我在2013年的报告中提出的观点:科学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是由相互竞争的利益所决定的。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家 Lipsitch 在本月早些时候与陈的布鲁金斯学会活动中强调了这一点。
Lipsitch 在活动中说:“我认为,我们对科学家的信任不应该多于或少于对其他人的信任。我们应该相信科学。当科学家讲科学时,我们应该相信他们,因为我们应该认识到他们是以证据为基础的方式说话。当科学家在没有引用证据的情况下表达政治观点或政策偏好甚至声称世界如何时,我们不应该给予这些科学家不适当的尊重”。
他继续说,在这些时候,科学家并不是在做科学。“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