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 Upping The Anti,作者 IAN LIUJIA TIAN】
2017年11月11日,在保安的帮助下,警察闯入广东工业大学的一间教室,逮捕了8名学生。作为一个左翼学生读书会的成员,他们当时正在主持一场关于中国当代左翼政治的讨论。被捕者之一张云帆在网上发表的帖子中写道:
「在我们被逮捕时的读书会中,我们正在讨论过去几十年的社会问题和历史,如工人的地位问题。我们在问:年轻人如何思考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我们确实谈到了二十九年前发生的事(指的是1989年)。但我们是 ‘太激进了’ 吗?当然,如果我们根据书本去定义 ’激进主义’ 的话。在中国,认识到社会问题就已经很 ‘激进’ 了;谈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则要 ‘激进’ 得更多。但是这个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社会问题,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为什么这是非法的?」
该读书会的领导人张云帆被指控 “扰乱公共秩序”,因为他们被逮捕时没有携带身份证。后来,警察冲进该读书会的共同组织者郑永明的公寓,逮捕了他,并把他关在警察局里。另一名受害者是孙婷婷,她因刑事指控被拘留。还有四名幸运逃脱的学生成员被警方通缉。
逮捕行动的荒谬性遭到了其他左翼团体的反对。事实上,统治的场所就是反抗的场所。 全国各地的左翼组织者以及香港的左翼组织者在线上线下联合起来,揭示了非法警察暴力的极端性及其矛盾的主张。更重要的是,那些被逮捕的人一旦被暂时保释,就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声明。警方没有料到这一点,因为他们认为学生会因为镇压的恐怖程度而保持沉默。最终,所有学生在2018年初被释放。
学生并不是唯一被警察盯上的人。例如,几位为珠江三角洲的移民工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的左翼律师在2016年底也被逮捕。这些逮捕和拘留表明,在后社会主义中国的背景下,围绕 “社会主义” 的定义展开了斗争。中国共产党(CCP)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由于本文的范围有限,无法全面解读中共对 “社会主义” 的坚称。然而,正如中国历史学家吴亦清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的那样,随着国家资本主义形成的展开,这种 “社会主义” 的宣称并没有任何社会公正的意义。为了回应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制定所谓的 “社会主义” 的,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些理论和实践,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历史依据的概念。
如果您错过了《中国特色的反共》
在后冷战和后社会主义时代的背景下讨论中国时,最好对两种归纳倾向都持谨慎态度。首先,是支持/反对国家立场之间的分歧。在没有充分了解复杂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项目的情况下,英语媒体,包括《异议》杂志这样的激进出版物,普遍认为任何反对国家主义的立场都是 “激进” 的。例如,像刘晓波这样支持自由市场的持不同政见者被打成 “右派”;而实际存在的中国新左派被指认为 “与中国国家合作”。其次,自由派和保守派媒体在描述中国时,都存在冷战时期的东方主义思维。冷战时期的东方主义被理解为冷战时期将共产主义国家 “他者化” 的延续,认为它们是 “反常的、极权的、野蛮的和不民主的”,因此,这些国家未能达到 “正常的、民主的和文明的” 现代性。研究中国的学者们经常从这样的角度来批评中国政府,把中国的资本主义描绘成 “失当的资本主义”,这是为了给新自由主义贴上“好资本主义”的政治品牌。
本文是针对这些流行的假设和二元论的反驳。接下来本文将首先对所谓的 “向资本主义过渡” 做一个简短但有历史依据的理解。第一节中提出的观点是,国家主义资本主义改革可能被理解为一场被动革命,以缓解文化大革命后的潜在群众组织化。第二,尽管全球资本主义的整合有助于稳定过去20多年来将 “社会主义” 作为一种话语部署的霸权政治精英,但主要在地下的理论和组织一直在发展,并为批判社会主义提供了可能性,这种社会主义类型有时与中共动员的国家社会主义话语有交集但也有分歧,一些左翼活动家称之为“皇马”(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本文希望关注的不是中国或中共是否仍然是 “社会主义” 的;相反,这里感兴趣的是将社会主义从霸权主义和中央集权的国家带回到工作场所、血汗工厂和社区的日常斗争中。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和阶级的一些说明
在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当前的新自由主义时刻被叙述为与社会主义过去的彻底断绝。威廉·辛顿、马丁·哈特·兰兹伯格、和大卫·哈维的作品都对市场化后广泛的阶级分化表示哀叹【参见马丁·哈特·兰兹伯格和保罗·伯克特,《中国与社会主义》(2005年);威廉·辛顿,《大逆转:中国的私有化 1978–1989》,(1990年)】
然而,这些理论假设:1)平等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就存在;2)资本主义转变的发生是因为毛泽东死了,“资本主义领路人” 邓小平获得了权力。然而这些假设不仅没有什么历史证据,而且也没有对资本主义改革是如何发生的、其背后的历史力量、以及中共领导人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决定改革进行系统地分析。
本节内容将提供一种理解,既不浪漫化毛泽东社会主义时代(1949年至1976年),也不否认其遗产。这种解释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内部霸权力量的转移和重组,以及来自不同战线的反霸权力量。首先,不平等现象在整个毛主义社会主义时代持续存在,资本主义改革只是对这些不平等现象的重组。详细来说,在1950年代初期和中期,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城市化并没有完全瓦解阶级。事实上,国家在没有监督机构的情况下直接控制资源,带来了新的不平等格局:1)高层官僚阶级比普通工人有更多机会获得政治和物质资源;2)只是理论上废除了私有财产,但实际上它创造了一种条件,即 一群政治精英通过控制中国的国家机器拥有生产资料。正如吴亦清所言,毛时代的中国农民和工人就像今天的农民工一样是无产阶级。
自1970年代末以来,国家主导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扩大了这些持续的不平等。更具体地说,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扩大了改革开放前已经存在的获得国家资源的不平等。私有化的过程产生了政治精英和资本之间的联盟,这可能被称为 “红色资产阶级”。在这个新的集团中,政治和官僚精英从他们对政治资源的垄断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以获取公共资产,最近还保护了资本主义的利益,那些主要是由于他们的政治特权而投资其中资本主义利益。
在过去的十年里,一个通过政府的恩惠和血缘关系(一些资本家实际上是政治精英成员的亲属)精心培养的资本家阶层已经变得很强大。例如,由万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联想集团、阿里巴巴(互联网零售商)、华谊兄弟传媒集团、复星集团、帆海集团等公司总裁组成的泰山会,是中国最神秘的资本家圈子之一。因此,将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视为党国主导的社会工程进程是很有成效的,“低透明度和低福利” 的国家背景使得党国必须扮演积极的市场代理人和工程师角色。
第二,市场改革可以被看作是中共内部政治精英为平息文革后的政治动荡而进行的一场被动革命。对官僚阶级获得国家权力和资源的政治化的不满在文革后得以持续。这种民众的不满正好与生产停滞和工作破坏的增加相吻合。
在文化大革命和1976年的四五运动之后,1978年出现了民主墙运动。许多地下出版物促成了中国主要城市越来越多的墙报,批评 “社会主义” 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一场继承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组织遗产的社会运动再次出现在地平线上。在这种深刻变革的边缘,政治精英们决定推进市场转型,作为 “解决人们挫折感” 的一个务实的办法。
这些反叛在1970年代末成为对政治精英的明显威胁;在这些强化的组织中,其领导人聚集在党的总部,宣布将党的目标转移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是市场改革的正式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1978–1980年对于党的方向乃至中国将要走的道路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之后的资本主义道路应该被概念化为对文化大革命所释放的人民自我组织的回应,特别是在更激进的派系中。
可以把资本主义的转变看作是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言之被动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为缓解基层民众的失望情绪和稳定其霸权地位而启动的战略。这些改革是以精心策划的方式进行的,以保持政治精英的完整。为向物质现代性过渡而设计的市场化不可避免地塑造了政府官员、普通中国人和中共的主观性。这些向资本开放的后果之一是加剧了阶级不平等,使全国的工人更加不满。另一个结果是反霸权的自我组织的崛起,它将具有革命性的和社会正义潜力的社会主义与作为国家言论的 “社会主义” 区别开来,后者缺乏社会正义和平等的意图(中共的意识形态)。前一种社会主义可以被称为批判性社会主义,因为它把社会主义带回了工厂和流民社区,提供了反霸权的潜力。
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批判性社会主义”
批判性社会主义是在当代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新左派、自由派和新儒家的讨论中出现的。中国的新左派是在冷战后的背景下出现的。新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汪晖多次质疑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追求;其他一些人如高阳和崔致远从1990年代开始就开辟了一个 “自由主义左派” 的话语。总的来说,新左派学者承认中国当代的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的直接结果;但他们在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方法上却有分歧。一些人希望毛泽东主义卷土重来,而另一些人则旨在在党国范围内构思摆脱中国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方法。
自由派主张建立一个不受政府管制的市场,并认为日益扩大的不平等是由国家的过度存在产生的 “黑帮逻辑” 造成的。新儒家思想是一种日益重要的新兴公共话语,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保留传统主义以解释中国经济的昂贵和竞争力的 “中国” 模式,是李光耀等多位国家领导人的知名表述。在中国之外,新儒家思想认为改革派中国终于 “回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轨道上”。例如,1989年之后,邓小平派代表到新加坡学习如何防止社会动乱的发生,儒家思想的复兴就出现了。
这些知识分子阵营塑造了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许多方面,然而却缺少基层的部分。事实上,知识分子的贡献往往忽略了普通工人的日常斗争,工人们表现出对正义和社会主义承诺的渴望。这种对社会主义的细微兴趣不同于1989年后经济新自由主义化所规定的自由派人格性,不符合国家社会主义的修辞。
社会主义的复苏,也就是此处所言之批判性社会主义,可以理解为源于基层组织的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尽管一些组织者可能没有明确地认定为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
批判性社会主义与中国国家修辞上部署的 “社会主义” 有什么不同?本节将概述批判性社会主义的一些关键点。最具潜力部分在于可称为基于社区的和本地化的社会主义形式。此处的意图是挑战惯常所谓的社会主义本身,并主张在后社会主义中国种族资本的破坏性后遗症中,关注批判性和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
谈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就会勾起人们对毛泽东时代的特别记忆。对于在改革时代(8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来说,毛主义社会主义代表了一个对中国现代性的残暴和破坏的时代。将 “社会主义” 与创伤和混乱联系起来,往往会促使改革后的一代选择消费主义所承诺的未来。政治精英 — 资本集团围绕着这种忘记社会主义历史的愿望,建立了它的权力和发展主义的理由。
批判性社会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将社会主义与中国党国脱钩的尝试。也就是说,我们正在见证一种反霸权的社会主义定义,它以劳工组织和工人权力为基础,而不是作为国家说辞的 “社会主义”。佳士事件就是这样一个例子。2018年,中国的左派学生前往坪山,支持一家名为佳士的公司旗下工厂的罢工工人。工人和学生要求建立独立的工会,提高工资,以及取消军事化的劳动控制。经过10天的激烈抗议,当地警方最终逮捕了罢工者和示威者。
佳士事件受到国际关注,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劳工组织的 “新时代”。然而,可以想象,这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持续的劳工斗争的结果。在21世纪初,一群毛主义者来到了珠三角地区,希望将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组织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努力越来越多,新招募的人员包括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工人。他们采取的一个策略是秘密地将地下劳工活动家安插在工厂工人队伍中。多年来,这一计划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劳工活动家仍然是零散的,成功的案例也是个别的。尽管如此,由于这些现有的关系,毛派学生和工人在最初的罢工开始几天后就迅速组织了佳士工人团结小组。
尽管如此,工人和佳士工人团结小组之间还是存在着围绕 “社会主义” 的矛盾。这种差异不应该被轻视。相反,它指出了这篇文章的核心:什么是社会主义组织?换句话说,工人的罢工努力能成为社会主义组织的一种形式吗?由于工人们并不精通社会主义或者毛泽东思想,因此很容易给出一个否定的答案。但作为一个组织者,应该知道以社区为基础和以工人为中心的方法是成功组织的关键,无论是否明确为社会主义。例如,工人们的挫折感来自于他们无法主宰自己的工作条件,无法形成独立的工会组织,这将是中国实现社会公正变革的第一步。
然而,团结小组的学生们却致力于社会主义,这种理论可能不会被工人们所认同。例如,在罢工前的整个互动中,社会主义的霸权话语从未出现在工人的讨论中。只有在毛派小组出现后,毛泽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口号才被调动起来。关键是要看到佳士出现的学生-工人团结,与工人自己指出的基于社区的社会主义可能性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
除了回归工人权力之外,批判性社会主义还通过与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其他基层社会运动合并而与作为国家言论的 “社会主义” 相区别。与以西方为中心的叙事方式不同,即 把劳工、女权主义、同性恋和变性人的解放按顺序和线性的时间轴排列,在后社会主义中国组织起来的工人已经是性少数群体和妇女运动的解放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相对于中共认可的社会主义有时在同性恋、变性人和妇女解放问题上的不足,批判性的、基于社区的社会主义一直在关注女权和性解放。本文作者所参与的一个团体就是这样的努力:酷儿工友(Ku’er Gongyou)。
“酷儿工友” 是一个为长三角地区的同性恋农民工提供服务的组织。它于2016年在苏州成立,旨在从左翼立场出发,促进同性恋的解放。坐落在农民工聚集的地区,它为许多被排除在车间圈子、乡村朋友和当地同性恋社区之外的人提供了宝贵的资源。除了组织像 “左翼看当代同志运动“ 这样的基层会议外,该组织还出版了他们的第一本书《社会主义与同性恋解放》,该书在香港和台湾有售,但讽刺的是,在中国大陆没有出售。
同性恋工人与其他同性恋团体的不同之处或许在于其对劳工和工人权利的奉献,在这一点上他们采取了国际主义的视角。2019年,在台湾为中华航空公司工作的飞行员进行了罢工。在一个罢工不是常见策略的国家里,这场斗争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酷儿工友” 虽然总部在中国,但却是唯一一个对航空公司工人表示声援的中国LGBTQ组织,并发表了一份由其他活动家签署的声明。他们的一些海报被分发到认同为性少数群体的农民工在线聊天群组中。
对于了解冷战时期中国地缘政治的人来说,“酷儿工友” 的举动意义重大。首先,资本是跨国界流动的,因此工人的权利也应该困扰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果说,“工人没有国家”,那么以国际工人权利为中心就会挑战民族主义的边界制造。关于台湾和中国的地缘政治辩论是紧张的对话,然而,这些讨论中往往看不到为台湾外包工厂工作的中国农民工与台湾工人之间的联系。“酷儿工友” 努力强调劳工斗争跨越国界的中心地位,确实为思考 “两个中国” 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方法。第二,“酷儿工友” 不顾国家调解的民族主义言论与台湾接触,是一个勇敢的举动。对于同性恋工人来说,团结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除非该地区的工人在各种优先事项中认识到他们彼此间的共同点,否则同性恋和社会主义解放将无法实现。
在妇女解放和劳工的交叉点上,“尖椒部落” 成为另一个重要组织。“尖椒部落” 位于珠江三角洲,为该地区的外来女工发布帖子并组织线下活动。作为一个由工人领导的组织,它为后社会主义中国的自由主义女权主张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替代方案。
例如,在2019年,该组织在深圳的工厂区组织了电影放映活动。不出所料,放映的电影是《美国工厂》,而不是《爆炸新闻》等影片。对于女工来说,工厂里的日常生活讲述了资本的暴力。电影结束后,在一些男女工人中流传的一句话是:“资本不姓中也不姓美,资本姓资”。
电影放映是一种富有成效的组织方式,因为工人可以看到自己是一个更大的生产系统的一部分,将自己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人联系起来。其他电影包括《女同工厂》,这是一部关于女同性恋移民工人要求工资的台湾电影。
此外,“尖椒部落” 还发布了由女性移民工人写的诗歌。这些诗集强调了全球种族资本的暴力,但也强调了对自由的渴望。这种基于欲望和女权主义的劳工问题处理方式,在后社会主义中国无疑是独一无二的。当代中国女权主义宣传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围绕着表达压迫和揭示创伤而展开的。与这些方法相反的是,女工们通过博客,写下了她们在工厂的旅程和她们的梦想。然而,通过叙述梦想,读者看到了为更好的生活和未来所做的日常斗争。例如,其中一首诗是由一个流民父母的子女写的,他也是一名流民工人,诗中写道:
—— 无题 ——
二十五年了
不明自己的来意?
像一片流云
风能吹散
雨能蒸发
软弱 无能 没出息
收好自己的标签
放在心底
论断淹没肉体
眼光穿刺灵魂
活下去
如果可以自由搏击
谁愿意用笔杆子书写愤怒?
如果有旷野厮杀
谁愿意做一头沉默的狮子?
这首诗是由一个叫季同(音)的年轻农民工写的,描述了摆脱束缚的愿望和自己所处的环境之间的障碍。从无根的失落感开始,描述了她在生活中被评判的日常经历。这些情况使她对自己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观产生怀疑。但是,尽管有障碍,她仍然坚持自己的精神。的确,她是一名斗士,一头需要解放的狮子。尽管她只能写作和保持沉默,但在沉默中,她愤怒了。
这首强有力的诗强调了在资本主义关系中自由的不可能性,但也强调了对解放的渴望,它为女工的组织和解放潜力提供了空间、时间和意向。尽管像写诗或放映电影这样的方法在北美的抗议现场可能被解读为 “去政治化”,但它们是后社会主义中国妇女组织的关键部分。
“酷儿工友”和 “尖椒部落” 等团体一直在努力为批判性社会主义寻找新的依据。他们的社会主义情感与党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话语完全不同。他们对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性解放和妇女解放的承诺,敦促他们从劳工斗争和工人组织的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这些都是具有革命欲望的批判性社会主义的重要课程。工人和学生再一次建立起关系,从中国党国手中夺回社会主义,但这一次他们特别关注性少数群体和妇女的斗争。
结论
“好的国家资本主义/坏的市场资本主义” 和 “不民主的东方/民主的西方” 的二元论,只是阻碍了当代激进的政治想象力。来自全球左翼的抵抗并没有以历史和背景知识来回应中国的复杂性。本文中所说的中国的批判性社会主义要求学者们将社会主义的定义多样化,并将国家组织的社会主义地方化为实现反资本主义解放的唯一合法途径。
像 “酷儿工友” 这样的团体和广东工业大学的事件表明,全球左翼必须在后社会主义中国的 “城中村” 景观中建立政治,而不是完全建立在反独裁主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批判性和基于社区的组织上。学者和活动家必须将自己视为自由主义项目的组成部分,该项目将中国打造成 “失当的资本主义”,以至于在种族资本、商品和人员的跨国流通中忽略了中国精英阶层的作用。
同样,政治经济精英在全球种族资本主义中的作用对于批判性社会主义的批判同样重要。就全球资本主义的灵活构成而言,废除全球资本主义和任何地方激进计划是相互构成关系。中国在全球种族资本主义中的崛起,与多种形式的采掘制度密切相关。例如,在2017年,采矿业是中国在澳大利亚投资的最大部门,然而这些做法中有许多是在原住民的土地上进行的。【毕马威和悉尼大学,《解密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2018年6月】
在加拿大,一个例子是中国国有企业中交国际有限公司收购爱康集团 Aecon 的失败。爱康公司参与了米克休克里族原住民社区领土的建设,以及 TransCanada 管道的建设。可以说,中国的收购与定居者殖民主义制度有关。
这种跨国资本的流动表明,全球团结是困难的,但却是非常必要的。通过概述批判性社会主义,本文将人们的经验和知识生产作为中心,而这些经验和知识生产在关于中国的地区研究和流行论述中经常被忽略。本文所描述的新兴组织形式将人们所熟知的社会主义地方化了。作为一个多元未来的占位符,批判性社会主义也许能从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后社会主义转型的经验中提供一系列的可能性。⭕️
Notes
The translation is mine. So are all the possible misconceptions and untranslatability. For the original text in Chinese, see Yunfan Zhang, ‘‘Wogui Renmin de Zibanshu (My Confession to the People),’’ 2018, from http://www.sdxf1917.tk/archives/20. ↩︎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Volume 1, trans. R. Hurle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101. ↩︎
See Sui-Lee Wee, ‘‘China Arrests Four Labour Activists amid Crackdown,’’ Reuters, Jan 1, 2016,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rights-idUSKCN0UO05M20160110; Chunhan Wong and Te-Pin Chen, ‘‘China: Court Sentences Labour Activist Lu Yuyu to 4 Years in Prison After Documentation of Labour Unrest,’’ Mar 27, 2019, https://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en/china-at-least-19-labour-activists-detained-by-authorities-china-labor-watch-releases-statement-on-those-who-assisted-lide-shoe-factory-workers. ↩︎
Yiching Wu, ‘‘The Strange Case of China: History, Class and Chinese Post-socialism,’’ Boundary 2 46, no.2 (2019): 153. ↩︎
Barry Sautman and Hairong Yan, ‘‘The ‘Right Dissident’: Liu Xiaobo and the 2010 Nobel Peace Prize,’’ Positions 19 no.2 (2011): 581–613. https://doi.org/10.1215/10679847-1331832. Although I disagree strongly with Liu’s politics, I do not think he should be jailed and kept in prison. My position is always in support of the abolition of the police and prisons, especially since I was also threatened and arrested by the Chinese police for my queer organizing work. ↩︎
.The “New Left” (Xin Zuo Pai 新左派) i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old, orthodox Maoist Left. Leading figures such as Wang Hui, Gao Yang, and Cui Zhiyuan perceive capitalism as the main factor contributing to an increasing rate of inequality in China and have been interested in collectivism in the socialist era. I have to note that these conversations happen outside of the Party ideology, but traces of writings seem to support state control of the economy. For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of the New Left, see François Lachapelle, Anshu Shi, and Matthew Galway, “The Recasting of Chinese Socialism: The Chinese New Left Since 2000,” China Information 32, no. 1 (2018): 139-159. However, the New Left remains a collective of predominantly male intellectuals and sidelines women’s issues in most of their discussions. For a discussion on the New Left’s neglect of women’s concerns, see Sharon R. Wesoky, ‘‘Bringing the Jia back to Guojia,’’ Signs 40, no.3 (2015): 647-666. ↩︎
Christina Klein, Cold War Orient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
For some liberal critiques of the Chinese state, see André Laliberté and Marc Lanteigne, ‘‘The Issue of Challenges to the Legitimacy of CCP Rule,’’ in The Chinese Party-State in the 21st Century, eds. André Laliberté and Marc Lanteigne, (Abingdon, UK: Routledge, 2008) 1-21; Peter Lorentzen, ‘‘Designing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Post-1989 China,’’ Modern China 43, no.5 (2017): 459–93; Xiaoguang Kang and Heng Han, ‘‘Graduated Controls,’’ Modern China 34, no.1 (2008): 26-55. DOI:10.1177/0097700407308138. For a critique of these liberal writings on China, see Patricia T. Clough and Craig Willse, ‘‘Human Security/National Security,’’ in Beyond Biopolitics, eds. Patricia T. Clough and Craig Wills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57. ↩︎
Yichi Wu, ‘‘Rethinking Capitalist Restoration in China,’’ Monthly Review 57 (2005): 44-63. ↩︎
Wu, ‘‘Rethinking Capitalist Restoration in China’’; Wang Hui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Chinese Neoliberalism: Another Discussion on the Ideological Situation in Contemporary Mainland China and the Issue of Modernity,’’ The Chinese Economy 36, no. 4 (2003): 10-13. DOI: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0971475.2003.11033470?journalCode=mces20. In Wang’s article, he details how bureaucratic manager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ld resources during the period of rapid privatization. ↩︎
Xie Lao, ‘‘A State Adequate to the Task: Conversations with Lao Xie,’’ Chuang 闯, February 2019, http://chuangcn.org/journal/two/an-adequate-state/. For an English source on the “Taishan Club” (the Taishan Industrial Research Institute, founded in 1994), see Li Cheng,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Xi Jinping Era: Reassessing Collective Leadership, (New York: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6), 174-5. ↩︎
Hui Qin, “Zhongguo Qijide Zaojiu yu Weilai: Huiguo Gaigeikanfan Sanshinian (The Formation and Future of the China Miracle: A Personal View of China’s Thirty Years’ Reform),” Southern Weekend, February 24, 2008,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7672.html ↩︎
Fulong Wu, ‘‘How Neoliberal Is China’s Reform?’’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51, no. 5 (2010): 625. DOI: 10.2747/1539-7216.51.5.619 ↩︎
Wu, ‘‘The Strange Case of China,’’ 151. ↩︎
Jo-his Chen, Democracy Wall and the Unofficial Journal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Studies in Chinese Terminology.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2). ↩︎
Yichi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Shaoguang Wang, ‘‘New Trends of Though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8, no.21 (1999): 197-217. ↩︎
Timothy Cheek, David Ownby, and Joshua Fogel, ‘‘Mapping the Intellectual Public Sphere in China Today,’’ China Information 32, no.1 (2018): 108. DOI: org/10.1177/0920203X18759789 ↩︎
Anshu Shi, François Lachapelle, and Matthew Galway, ‘‘The Recasting of Chinese Socialism,’’ China Information 32, no.1 (2018): 147. doi.org/10.1177/0920203X18760416 ↩︎
For some liberal publications that espouse the market, see: Xueqing Zhu, Daodei lixiangguo de Fumie (The End of a Moralist Utopia),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2003); Jinglian Wu, ‘‘Zhongguo Gaige Jingru Shengshuiqu: Tiaozhang Quangui Zibenzhuyi (China’s Reforms Have Entered Deepwater: The Struggle Against Crony Capitalism),’’ Luye (Green Leaf) ½ (2010): 90-5; Weiying Zhang, “The New Enlightenment of Reform: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Propelled by the Market of Thoughts,” (Beijing: CITIC press group, 2014). ↩︎
Ya-Chung Chuang, ‘‘Democracy Under Siege,’’ Boundary 2 45, no.3 (2018): 70. ↩︎
Arif Dirlik, ‘‘Forget Tiananmen, You Don’t Want to Hurt the Chinese People’s Feelings, and Miss Out on the Business of the New ‘New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5, no.2 (2014): 304. ↩︎
Lisa Rofel, Desiring Chin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25-6. ↩︎
Note that the CCP does have a national union, the 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ACFTU). Independent unions are illegal. ↩︎
See the website for the Jasic Workers Solidarity Group: https://jiashigrsyt1.github.io/727oneyear/ ↩︎
It remains to be seen how independent unions can work within a state that seeks to confine workers within the existing ACFTU. It is also worth noting that many workers in China are not unionized, such as those in temporary jobs, factories, and domestic work.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space for this article, these discussions are unfortunately not elaborated. ↩︎
Personal Communication with Shen. ↩︎
The older cohort, mostly those who lived through the Maoist socialist era, tend to invoke Mao’s writing and thinking when they voice the support of workers’ struggles in the post-socialist present. ↩︎
See their website: https://site.douban.com/29 3169/ ↩︎
For the poem in Chinese, see: http://jianjiaobuluo.com/content/107590 ↩︎
John Holloway, ‘‘Global Capital and the Nation-State,’’ Capital and Class 18, no. 1 (1994): 23-49. ↩︎
The attempted buyout was blocked by the Canadian federal government, but the fact that Chinese capital tried to fund a company implicated in the settler-colonial project is indeed troubling.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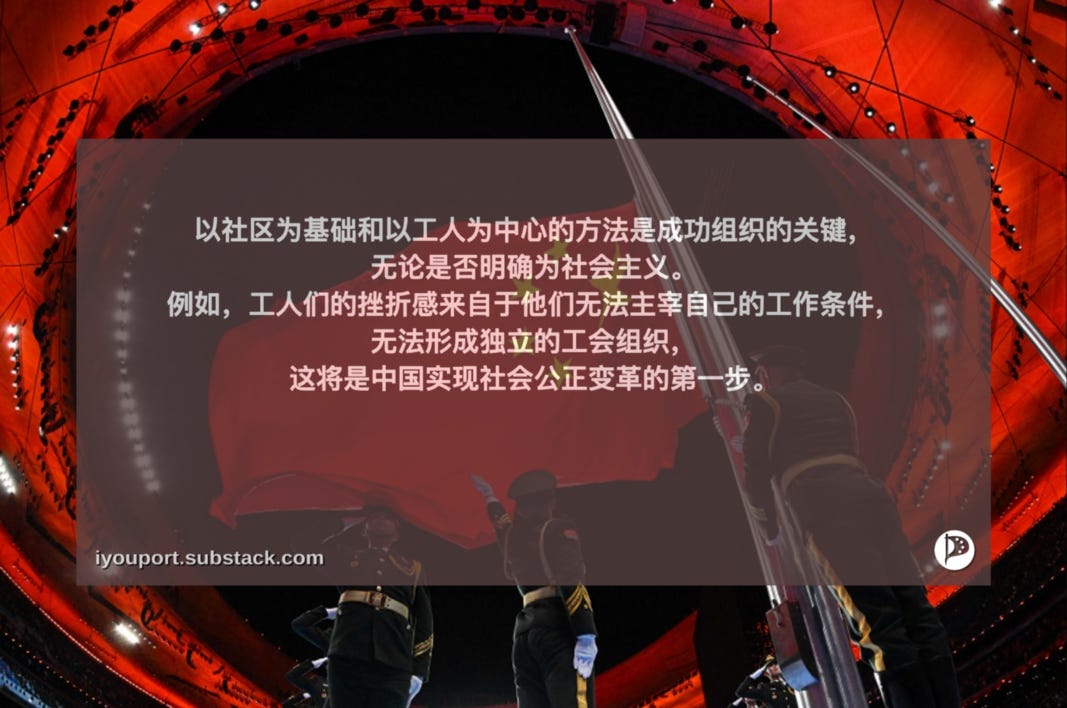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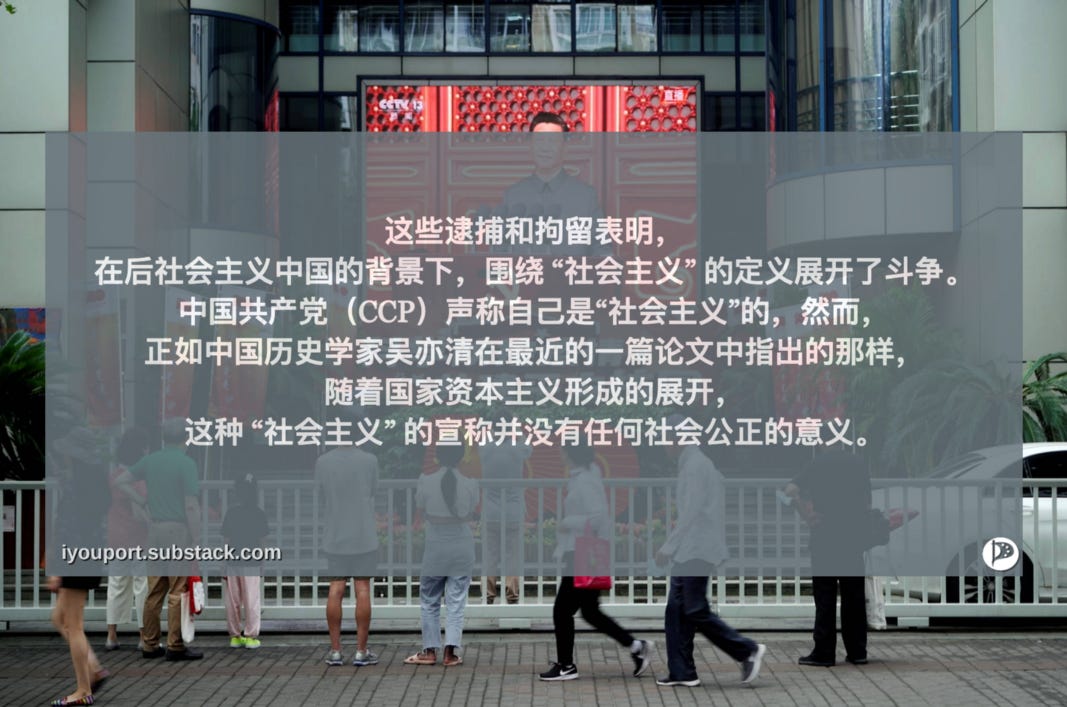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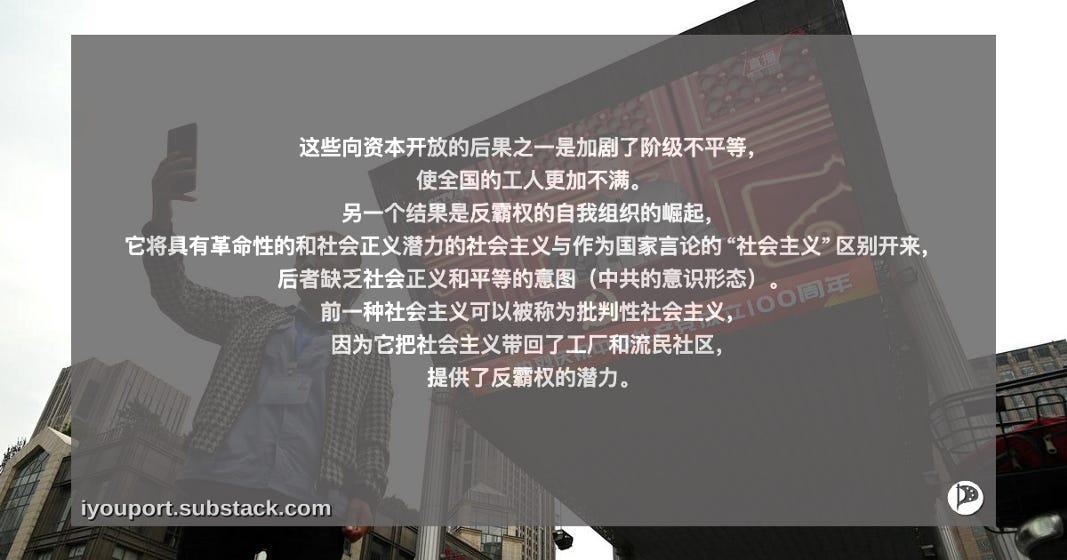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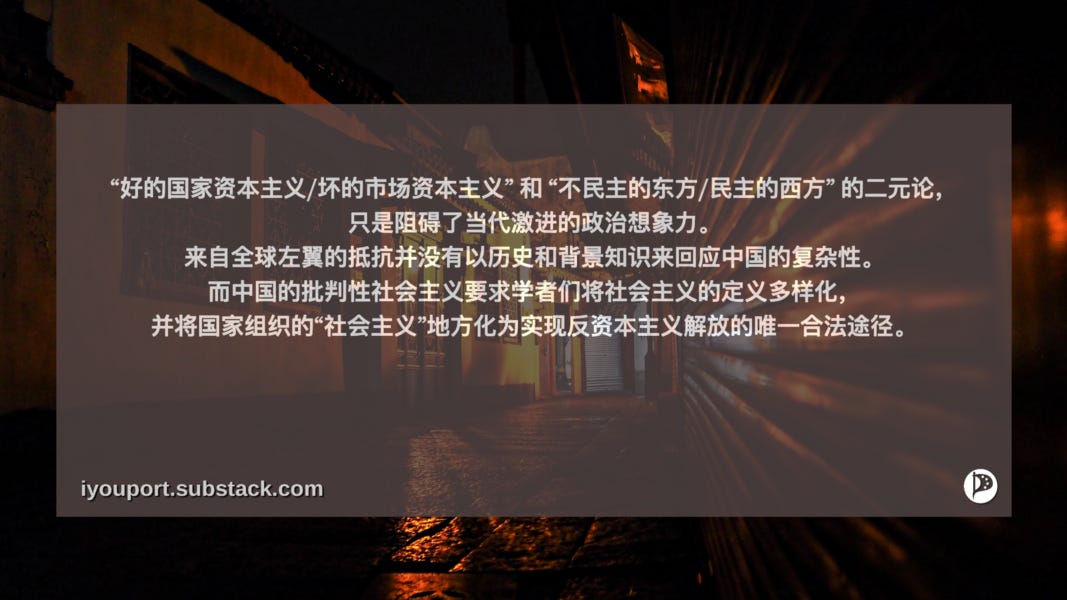
这篇终于放出来了,27号当年邮件就提示我更新,但是网站上一直没有,好多天IYP都没更文章了,我还以为你们出了什么事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