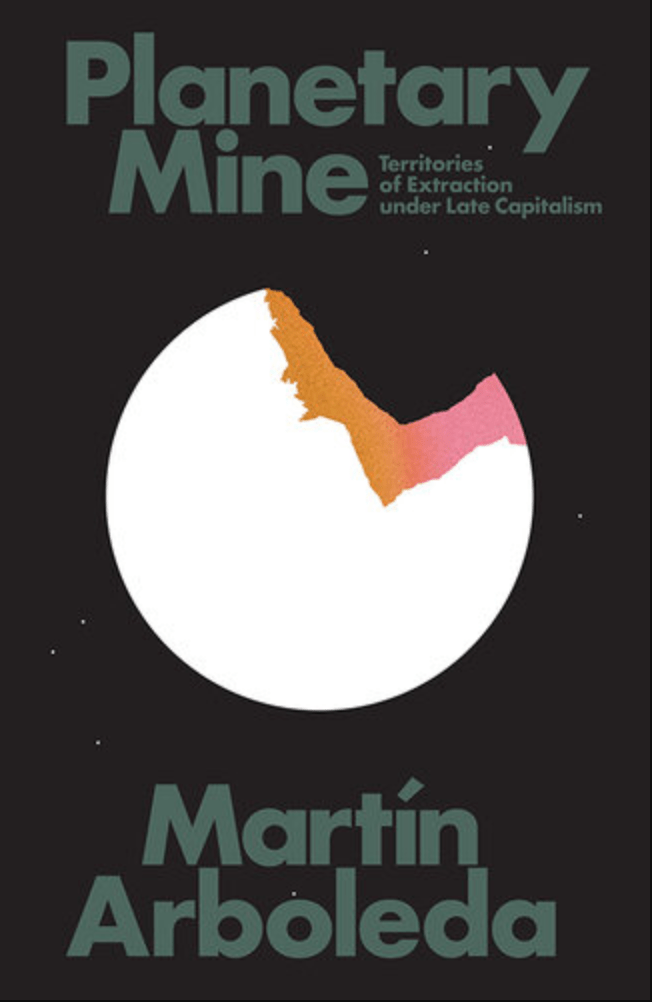【按】从监视资本主义到气候危机,从剥削奴役到暴力镇压,从严重的不平等到针对“低端人口”的驱逐,从右翼民族主义夺权到新帝国的崛起,从零日漏洞作为武器的跨国销售和网络战雇佣兵,到邪恶监视技术的全球销售和使用、集中营泛滥和民主的衰竭 …… 这个时代的几乎所有标志性灾难都并非任何一个国家的特例,相反,它一旦发生,便在整个星球上蔓延。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当下的反抗,如果只针对本土的眼下问题,您将很难取得真正的成功。最好的结果是,您将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进行相同的战斗,在原地打转;最坏的情况是,任何一场甚至是虚假的胜利,都无法赢得,您的努力只是在加强对手的利益。
如果您的反抗致力于解决问题,您就必需准确抓住问题的根源。
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如何爆发的?移民危机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本土反抗依赖地缘政治竞争关系是错误的?为什么反抗者的跨国联盟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合同工、流民潮、强迫劳动、暴力镇压的日常化、民族冲突频发,这一切的背后是什么?
您将在、也只能在全球视角下看清这些问题。
尤其是中国的反抗者,因为你们处于一个 “要塞部位”。
帝国主义就是全球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方式,这本书的论述再次印证了中国的银河帝国及其对人权的侵犯和对少数族裔的压迫,正是全球资本主义及其政治保护伞的产物。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倾向于更多关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环保运动、数字技术反叛,因为它们可以切中要害 —— 它们重新利用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强加的以技术为媒介的相互依赖关系。
直接行动几乎是唯一的方法。
本文中讨论的书籍您可以在这里下载:《Planetary Mine: Territories of Extraction under Late Capitalism》(2020),以及《Expulsions: Brutality and Complex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2014)。
全球化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很难确定这种冲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概念以及它所把握的进程,几乎与围绕它所展开的争论同步。
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日子,也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向墨西哥政府宣战的日子;在美国,另类全球化运动在1999年的西雅图之战中爆发;在2005年,巴西阿雷格里港的世界社会论坛达到顶峰,注册人数超过15万人。
【注:世界社会论坛又称社会运动论坛世界峰会,是反全球化运动与另类全球化运动成员的年度聚会。成员们利用此聚会来联合全球活动家、分享与讨论组织战略及互相交换关于世界各地与自身议题的运动资讯。 】
几年后出现了 “广场运动”,抗议者占领了从雅典到纽约到开罗的各种公共场所。这些事件与拉美地区反抗自由贸易和美国霸权的整个时代相吻合,最终形成了 “粉红潮”,这又预示着左右两派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虽然它们的诊断结果截然相反,但针对的都是市场民主国家无趣的管理主义。
【注:粉红潮这一概念是 Larry Rohter 首次提出,他在报道2004年乌拉圭总统大选时形容该国候选人塔巴勒·巴斯克斯并不是纯粹的鲜红色左派,而是更加温和的粉红左派。】
【注:管理主义讲究对权威的服从,因为人们愈是服从,管理起来愈是方便。 “要做乖小孩”、“服从为负责之本” 等格言皆能代表管理主义的规训。 管理主义旨在增加人们的一致性和集体性,使他们服从权威。】
而这一切仅仅是个开始。
在经历了社会运动和金融危机的动荡之后,“平地乌托邦” 的命运 — — 一个由和平贸易、数字通信和国际机构的筋脉连接起来的全球人类的梦想 — — 在仁慈的美帝国的保护下,进入了另一个不确定的阶段。
在多个大陆,由新自由主义培育的右翼民族主义夺取了国家权力。贸易战、退出多边主义、重构历史性的联盟,接踵而至。当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出现时,全球一体化已经出现了低谷,然后通过跨国互联的途径四处蔓延。
以无摩擦流通和及时生产为前提的供应链陷入停顿;与此同时,各种意识形态的政治领导人都在哀叹 “依赖”,不仅是对中国的依赖,而且是对全球分散化生产本身的依赖,这些生产制造了从表面的(快时尚)到基本的(个人防护设备)的一切。
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呼吁 “改制” 供应链,将生产规模缩减到国内和地区层面,并在经济效率和新的公共卫生紧急需求之间取得平衡。
我们是否正在目睹全球化的黄昏?
在资本主义下,表象总是具有欺骗性。拆解遍布全球的开采、生产、分配和金融的过程将被证明是一项复杂得令人困惑的任务。
这些过程以运输技术(集装箱化、多式联运)和计算技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机器人)为中介,安排在不同的经济地理区域(走廊、门户、集群、经济特区),由不断发展的企业间和企业内部关系(外包、分包、垂直整合) 和市场力量形式 (垄断和独占) 构成;最终由国家权力机构促成,国家权力机构提供必要的后勤和监管基础设施,以及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货物流动的镇压机器。
“全球化的资本主义” 近乎于一种矛盾的说法。自其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和土著人被剥夺的情况下诞生以来,利润的逻辑施加了一种离心力;积累的动力是一种空间上的整和。无论在理论上有什么可能,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总是依赖于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不均衡的廉价化,在无情的生产祭坛上牺牲遥远地区的生命和生态系统,以及不断驱逐 “过剩的” 和被过度利用的 “低端” 人口。
因此,民族主义的退缩是一种幻想。但幻想在政治上可能是强大的:在实践中,“把制造业带回家” 的呼声预示着一个严峻的世界,这个世界对移民的管制更加严厉,供应链越来越被国家暴力所保障。
今天左翼的任务是掌握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基本全球规模,以及我们转型项目的全球视野。马丁·阿尔沃莱达在《Planetary Mine》中严谨而慷慨地描绘了这种全球性的相互依存关系 — — 其残酷的现实和解放的可能性。通过对从智利到中国的无垠采掘区 — — 矿山、炼油厂、港口、船舶、发电厂、数据处理中心、以及作为资本物流中心的整个城市 — — 的有利位置进行描绘,阿尔沃莱达不仅将边缘拉近中心,而且填补了我们贫乏的空间词汇。世界体系的边缘远非落后:它们是新的开发技术的所在地,也是底层未来主义的先锋。
零碎的利维坦
这个行星矿的碎片随处可见。鉴于水管装置、电线、窗户等材料的来源,城市景观是一个 “倒置的矿山”:摩天大楼不仅用开采的材料建造,它们本身也是由最初为地下开采发明的照明、通风和电梯装置构成的。这些碎片也存在于 “几乎难以察觉的实践和习惯中,…… 编织了日常生活的结构”;稀土、锂、钴、镍和铜是无数电子设备的基本成分。行星矿不仅使我们的浪漫邂逅和日常锻炼成为可能,也使国家监控和劳动纪律的领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技术进步是用来提取的产品和工具。正是由于 “机器人化和计算机化的飞跃”,采掘领域不断扩大,包括高耸入云的安第斯山脉的山峰,以及更有想象力的海底矿物资源和近地小行星的星外矿藏。
矿物源养活了机器,而机器又能提取更多的矿物。人类的劳动 — — 无论是在矿场和物流中心周围大量涌现的非正规服务部门的低端工作,还是工程师和程序员日益无产阶级化的专业工作 — — 都作为技术设备的附属品发挥着作用。
随着拉美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量不断增加,自动化的步伐也在加快,2000年至2011年,中国的贸易量增长了13倍以上。其中大部分是由拉美的矿产、大豆、石油和牛肉组成,将这两个地区锁定在一套密集的 “社会经济相互依赖关系” 中。给大家一个规模感:“Valemax” 号从中国运输煤炭到巴西,回程运输铁矿石,是 “世界上最大的散货船”,运力达45万载重吨。阿尔沃莱达的描述渲染了一种工业的崇高,同样是 “可怕和令人敬畏”,让人想起维多利亚时代的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和吸血鬼的兽皮书 — — 尽管有赛博格的更新,比如机器人化的 “巨型推土机”,可以 “在高海拔、零能见度、和恶劣天气的条件下作业”。
当然,只有与劳动相结合,机器才会发挥其生动的力量。
自1992年以来,4亿中国农民被强行 “非农化”,被安排在工业工厂工作;在太平洋的另一边的美国,农民和土著人也被赶出他们的土地。马克思将这一过程称为 “原始积累”:强行将人们从他们的生存手段中分离出来,迫使他们从事雇佣劳动和现金交易。
阶级结构的这些变化并不是平行展开的,它们是有内在联系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取决于对拉美农民的剥夺 — — 以及贪婪的采掘和超级农业所带来的森林砍伐、污染和癌症流行。阿尔沃莱达认为,这种共同的压迫是他们获得解放的共同条件的线索。
中国工人和智利工人之间的共同点比他们与各自的统治阶级之间的共同点要更多。 而且,作为对 “恐中症” 的一个有益的纠正,中国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一心想要统治世界的阴谋霸主;相反,借用斯图亚特·霍尔的说法,帝国主义就是全球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方式。在这种解读中,中国的银行和公司在扩大采掘领域中的作用恰恰是这个全球性进程的表现。
【注:斯图亚特·霍尔 (Stuart Hall) 英国文化理论家与社会学家,与理查德·霍加特及雷蒙·威廉斯为现在的现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建立者之一。 1995年到1997年间担任英国社会学协会会长。】
从这一行星角度来看,传统的世界体系理论中的 “核心” 和 “外围” 类别并没有映射到以国家为界的单位上。它们反而存在于一个跨尺度重复的分形关系中。
阿尔沃莱达关注的是城市。在智利,这个行星矿场在 “迷茫、干旱、断裂的城市景观” 中展开,北部沙漠地区 “财富与贫困并存”。安托法加斯塔市构成了矿业经济的一个关键节点;其城市空间作为一个基础设施,使采矿供应链中的 “流动、连接和速度” 得以实现。在产品、劳动力和资本无缝流通的背后,是 “港口起重机、货船、火车、卡车和产业工人的疯狂流动”。
城市和工人的存在都是为了服务于已故的加拿大哲学家莫伊谢·波斯顿所说的积累的 “跑步机”。
【注:莫伊谢·波斯顿(Moishe Postone)是加拿大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他曾是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在那里他是犹太研究委员会的成员。“跑步机” 在这里也指单调繁重的工作。】
景观和劳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资本密集型开采及其支持性的物流基础设施所改造的同一建筑环境带来了 “集体劳动者”,这个内部异质的有机体由工程师和家政工人、编码员和卡车司机组成,他们居住在由光鲜的塔楼和污染的棚户区组成的隔离景观中。
货物畅通的另一面是工人面对的无情的不稳定。这种情况既存在于工作中(智利大多数港口工人都是临时合同工),也存在于不安全的城市住区为主的家庭领域中。将这些 “僵化的空间” 与供应链物流的 “自主机械装置” 缝合在一起的是国家。技术官僚的管制和压制力维持着这个跑步机继续运转。
资本的咽喉
国家权力为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在智利,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残暴的新自由主义独裁统治时代(1973–1990年)的法律框架将水转化为商品,将国有公司私有化,并建立了采矿特许权制度,以使农民和小业主的土地被征用。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自然财富被转移到资本家手中,为智利所谓的 “经济奇迹” 奠定了基础。
私有财产的创造和市场交换与暴力的 “驱逐逻辑” 并驾齐驱,国家的合法性是基于技术官僚机构在军事暴力领域的体制隔离。但这种武力部署并不仅仅是历史的产物,它是所谓的 “经济自由” 的持续保障。国家和资本在组织上的统一表现是 “对纠察的港口和矿工派遣的警车、释放的水炮和催泪弹”。事实上,矿工反叛 — — 它与弹性化的劳动制度同步产生 — — 构成了官僚机构和私营企业的供应链管理者的主要关注点。正如 Deborah Cowen 所言,自军事化物流起源以来,供应链总是将资本和强制力结合在一起。在 “9–11” 事件后的时代里,这些全球网络受到一种安全逻辑的支配,这种逻辑将工运罢工、所谓的恐怖主义、和海盗行为等同于对货物通过跨国 “走廊” 和 “门户” 快速流动过程中的诸多威胁。
要抵制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更不用说改造它了,是令人生畏的。但阿尔沃莱达这本书从工人、农民和土著人民反剥削、反抢占、和反污染的抗议活动中找到了希望。他认为这种 “平民” 的大众主体不是一个浪漫的、前资本主义的群体,而是一个集合体;一部分是人,一部分是机器,这个反叛的集体重新利用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强加的以技术为媒介的相互依赖关系。
资本可能是一个弗兰肯斯坦的怪物,但资本自己的怪物是它所释放的解放主体。当工人和社区举行罢工,破坏基础设施,占领矿井和他们所吞噬的更广阔的领土时,他们主张对人员、商品和利润的流动进行控制。这些行动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它们暴露了国家和公司权力的相互交织的整体性。
矿场的斗争超越了狭义上理解的劳工不满。在2006年抗议者占领由几家外国公司经营的埃斯康迪达铜矿期间,工人工会与女权运动联合建立了一个营地,举行集会,演奏音乐,传授激进的反抗者教育学。
民众政治也超越了矿山本身。在2001年 Pascua Lama 金矿开工后的长期冲突中,直接受影响的农民社区是关键的主角。瓦斯科山谷的居民通过各种农业、土地保护和环境团体动员起来,采取直接行动 — — 包括破坏采矿基础设施 — — 以及组织游行和出席巴里克黄金公司的股东大会,谴责该公司对人民生计和生态系统的威胁。这些行动已被证明是有效的:该矿已有三年未投入运营。反抗组织的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也许与阻止该矿的开采同样重要:受影响的社区建立了一个跨地方的集体行动者联盟,使他们被疏远的相互依存关系从资本的支配下解放出来。
这些形式的民众力量具有真正的影响力,在关键的节点处减缓了开采主义的发展。复杂性是当代供应链的优势,但也是其脆弱性的来源。弹性和风险交织在一起。供应链的每一个节点都是技术故障、劳工反叛、土著抗议,以及越来越多的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天气的潜在地点。这个星球上的矿井使阶级斗争的据点倍增,从港口到矿山,从棚户区到法院,抗议声四处回荡。这种斗争指向资本在不停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所结合的 “人、生态和技术” 之间的关系的激进式重新排序。
关于采掘的著作往往关注私人公司、政治压迫和披金戴银的精英世界,或者关注当地社区的基层动员。而这本书则两者兼而有之。阿尔沃莱达对剥削的审问在强度上与他对 “未来技术景观的梦想图像” 的忠实相匹配。乌托邦在黯淡的当下无处可寻,但其成分却在我们的视线中随处可见。
虽然供应链斗争的地点多种多样,战术也多种多样,但这本书中没有直接涉及的一种可能性是,抓住国家机器的要素,强制调整经济方向,从开采转向社会生态繁荣。这种可能性在这本书以智利为中心的分析中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尽管一波又一波的民众起义,最近一次是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初,智利政府已经证明了它在转移和分裂左翼政治力量方面的灵活性。
智利绝非特例,而是全球镇压的模版,这本书应该给所有受压迫者提供战略思考。还是那句话,《要运动,不诉求》。
阿尔沃莱达的国家怀疑论也是他严格理论化的产物,他拒绝接受拉尔夫·米利班德和尼科斯·普兰查斯在1970年代国家辩论中的立场。简单说,前者认为国家是资本的工具,后者则认为国家与统治阶级 “相对独立”。与二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尔沃莱达强调了国家与资本的组织统一性,和全球视野的重要性。国家对统治阶级自主性的主张既是 “虚幻的,又是真实的”;这种矛盾实际上是其合法性力量的条件。他写道,民族国家是世界市场的 “等量部分”: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而不是离散的单位。
这句话非常重要 —— 正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当下的反抗如果继续聚焦于本土的眼下问题,是很难成功的。
此时此刻
“行星矿” 展望了一个革命的地平线,在这个地平线上,我们所知的雇佣劳动和国家都被废除了。阿尔沃莱达所叙述的反抗运动肯定阻碍了采掘业的发展;然而,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制度化,这种微小的胜利仍然是临时性的、预设性的,反抗者所想象的未来将永远被推迟。
在世界其他地方 — — 在过去的其他时候 — — 左翼政治运动已经夺取了国家权力,并试图改变社会,但成功和激进程度各不相同。这些实验提出了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棘手问题,从议会制路线到社会主义、到双重政权,再到尚未发明的概念,以及每种方法的陷阱。但在一个气候灾难加速、不平等现象惊人、民族暴力频发的世界里,很难想象有一条不经过国家的转型之路。
如果民族国家如阿尔沃莱达所正确地论证的那样,是 “其规模是全球性过程的集中体现”,那么它不也因此成为了普遍化的阶级斗争的地形吗?如果资本和国家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整体性,那么夺取对国家及其代表、监管、金融和法律机构的控制权,就是在争夺资本对投资、生产和分配的控制权的一种手段。绿色新政就是在这一战略的推动下进行的 — — 正如目前在拉丁美洲势头强劲的 “生态社会公约”(以及阿尔沃莱达目前关于农业供应链的研究,它明确提出了国家权力和经济规划的问题)。这些转型项目提出,气候正义只有通过议会制之外的斗争和左翼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
资本主义是气候危机的虬结根源。绿色资本主义尽管在术语上是完全矛盾的,但它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是,没有国家的干预,经济的生态优化调整是不可能做到的;问题是它将采取什么形式?为谁的利益服务?
在欧盟,官员们正在制定我们可以称之为气候智能型资本主义的纲要,利用公共资金和监管鞭策相结合的方式,推动投资者向绿色产业发展。产业政策的方法是将风险和初始投资社会化,但同时将利润私有化。这是在世俗停滞时代给资本的礼物 — — 老黄瓜刷绿漆。
生态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是什么?阿尔沃莱达有力地反对民族主义,无论是政治还是分析。这是令人信服的。就像《行星矿》中详述的采掘回路一样,风力涡轮机和电动汽车等绿色技术的供应链将可以而且必须跨越国界:制造这些技术的资源在地壳中沉积不均,左翼的承诺应该瞄准全球准入,这意味着优先考虑全球公平分配。广泛的生产网络就是21世纪行使民众权力的战略节点。
从智利土著人对锂矿开采的封锁,到美国特斯拉工厂的劳工组织,全球的社区和工人正在抵制新生的绿色资本主义,并想象着另一种绿色未来。这种抵制是生态社会主义转型的必要条件,但仍是不充分的条件:在避免最严重的气候混乱的十年时间里,国家有能力在此时此刻调整经济活动的方向。公共投资、民主化的金融、严格的法规、公有制和工人所有权、贸易和产业政策,都可以在建设民主化的、低碳的未来中发挥作用。在社会运动、工会和跨国联盟行动者的手中,这些工具可以从垂死的旧世界中塑造出一个新的世界。
从地球上的矿场到全球工厂,未来供应链的组织结构是可以争夺的。与国家权力并肩作战、反对国家权力和争取国家权力的草根斗争,将有助于塑造即将到来的经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