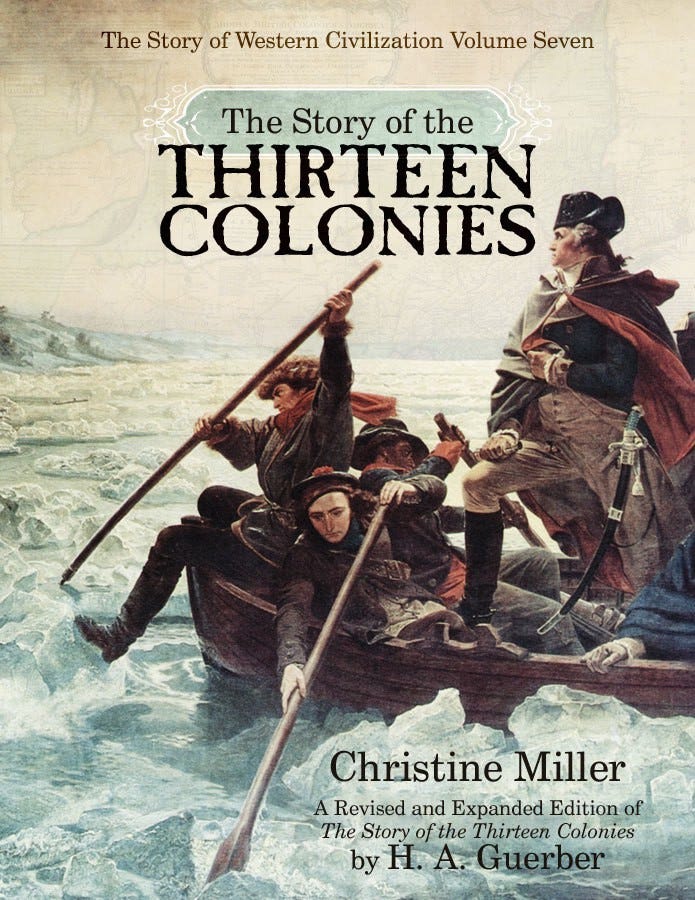The love of one's country is a splendid thing. But why should love stop at the border? - Pablo Casals
可能很少有人记得,在一代人之前,学者、银行家们组成了一个响亮的大合唱,宣称国家已经过时。资本、思想和货物的流动迎来了一个具有新的隐喻和关于全球化、运动和流通的新叙事的全球时代。
而现在,“全球” 的承诺和情节线看起来已经过时了。国家又回来了。
乏味的、以种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品种并不是唯一的复兴;在自由派和进步人士中,作为最需要治愈的社区,“祖国” 的概念也在崛起,以便从本土主义者手中 “夺回” 它。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全球主义忽视和最近的本土主义滥用之后,有一个新的合唱团给它提供了叙事上的提升,而这正是国家需要的。国家需要一个想象中的过去,将他们的公民与共同的经历联系起来;国家建设者创造了这一叙事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墙壁和屋顶。为了愈合 — — 有人会说,为了掩盖 — — 裂痕,新一代编年史家们争先恐后地重建这些基础。
进步人士可能认为,这种开垦是对本土主义的英雄式反击。而事实上,这是对失败的承认。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失败。首先,随着冷战的结束,许多自由主义者投身于市场统一世界的承诺,甩掉了社会福利和社会民主的 “包袱”。然后,随着全球化在2008年后开始动摇,本土主义的反击者夺取了反对 “全球主义” 精英和 “威胁性” 移民的旗帜。现在,进步人士正跳入国家故事情节的坑中。
在每一步,进步人士都采取了防御措施;在每一步,他们都放弃了一些东西。到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1989年后,他们把社会主义遗产的剩余部分兑现了。自2008年以来,许多人正在放弃他们的国际主义遗产。随着气候危机的袭来,全球移民危机加剧,核军备竞赛升温,那些试图赎回国家的编年史家们正在我们需要的时候退出对全球视角和叙事的探索。
两个世纪以来,国家一直是所谓主权概念的组织原则,并且从一开始就被捆绑在一个更广泛的秩序上。在18世纪,杰里米·边沁创造了 “国际” 一词,以设想民族国家的纠缠来取代掠夺性帝国的无序。国家独立宣言是相互依存的宣告,是希望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和欢迎 — — 从而确保自己的自由 — — 并保证自己愿意受到约束以维护更广泛的秩序。它是国际法的基础,以至于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除非是那些根据定义被排除在承认和自由之外的殖民社会。当它们发挥作用时,国际法和规范确保了国家不会成为掠夺者。当它们失效的时候,“国家第一” 的狂热就占据了上风,原本应该相互依存的关系被武器化,国家的需要被授权进行征服和灭绝。这就是1930年代发生的事。
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命运是一起前进的。技术变革和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一个根本性的突破,我们仍在努力理解。它们带来了最后一轮的非殖民化,在拆除资本和商品流动的障碍的同时,将地球上的国家覆盖起来,在加深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同时,扩大了国家。一波自由贸易协定和移动支付带来了新的仪式 — — 世界经济论坛、和机构 — — 世界贸易组织(WTO) — — 来庆祝连接性、流动性和超资本主义的共享时间感。不受地点的限制,新的大亨们寻求 “为我们所有客户的需求提供跨地域的服务” — — 用美林证券1994年的一份招聘手册的话来说。
经过两个世纪的英雄主义和恐怖,国家被淘汰。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爱国主义被置于世界杯和法老式奥运村的安全阀中。历史学家们也加入了这一行动,扩大规模,做大做强,走向全球,把国家的故事换成网络,把公民换成连接。
在一个温度升高且现在瘟疫肆虐的世界中,公民只能在国家的怀抱中寻找庇护所。
当地平说的使徒们幸灾乐祸的时候,民族国家的语言变成了抵抗的修辞,尤其是在全球化没有覆盖到的南方。在阿根廷,人们抨击紧缩政策对公民和债权人的粉碎性影响。台湾企业进入种族隔离后的南非,雇用被剥夺权利的工人进入他们的价值链,使工会和社区领导人与急于获得投资的新兴非洲人国民大会(ANC)政府对立。1997年中期,一名抗议者对陷入困境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理事会喊道:“我们已经让你们上台了,现在你必须兑现”。然后,在很大程度上被保留在全球边缘地区的不满情绪回到了其核心地区。2008年的经济危机使无国界世界的想法失去了光环。自2009年以来,国旗一直是世界范围内抵制世界性精英和难以捉摸的世贸组织贸易争端机制及其技术官僚的标志。
爱国抵抗运动的复兴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它同时发挥了两种功能。它是一个反对 “全球主义” 和 “达沃斯人” 的信息;它还宣称谁属于这个国家,以应对被煽动起来的对移民和少数民族的恐惧。当 Nigel Farage 等英国脱欧派政客嘲笑布鲁塞尔的监管机构时,这是为真正的演出所做的热身表演:大谈移民的威胁,他们沿着巴尔干半岛前进,入侵拿破仑和希特勒之前失败的地方,因为欧洲已经放弃了国家的概念和站在它旁边的大多数民族。为了将英国民族从 “种族灭绝” 中拯救出来,它必须从欧洲分离出去。
歇斯底里并不限于 “西方”。在印度,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也在追寻同样的弧线。自从2002年古吉拉特邦发生血腥骚乱,造成约200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穆斯林,莫迪就受到了欧洲使节的非正式抵制。随着他在印度的崛起,而马琳·勒庞和马泰奥·萨尔维尼在欧洲的地位上升,回避莫迪和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变得更加困难。2013年1月,扭扭捏捏的欧洲外交官们欢迎莫迪参加在德国大使馆举行的秘密午餐。6个月后,莫迪推倒了他们的疑虑:“我是民族主义者。我是爱国的。没什么错”,他在赢得印度人民党的领导权和国家总理职位的过程中感叹道。
在一个竞争激烈、温度升高和现在瘟疫肆虐的世界中,公民们只能在国家的怀抱中寻找庇护 — — 并被召唤去保卫国家。大学和学校已经成为国家叙事的战场。在去年夏天的BLM示威活动之后,当时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成立了一个1776委员会,以庆祝 “爱国主义教育”。在阿肯色州和其他地方,拟议的立法将惩罚那些将白人至上的历史作为美国历史的一条主线来教授的学校。土耳其政府已下令开除了近6000名 “不忠” 的学者。在香港,约3000名学生被捕后,北京的警长林郑月娥谴责该市的校园如何未能教授正确的国家价值观。“香港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她哀叹道。与此同时,共产党重申了其爱国主义的说法。香港教育部长禁止学生唱《光荣属于香港》,取消了名为 “通识教育” 的公民教育必修课,并规定必须教授中国历史。同时,图书馆正在清理任何所谓的 “危及国家安全” 的东西。历史教科书必须培养 “对国家的归属感,对中国人民的感情,对国家的认同感,以及对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感的认识”。
1940年夏末,乔治·奥威尔进入了他最黯淡的时刻之一。这位曾在巴塞罗那与无政府主义者并肩作战的作家和国际主义者,一旦斯大林与希特勒结盟瓜分欧洲大陆,就不得不考虑自己信念的局限性。法国沦陷后,奥威尔在《我的祖国是左还是右》(1940年)一文中宣布了他的转变,他愿意穿上文学制服来保卫国家。对他来说,敦刻尔克的灾难更证明了英国统治阶级的缺点。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奥威尔把英国比作 “一个由错误成员控制的家庭”。不过,他还是团结在国旗下了,因为只有国家才能唤起对抗法西斯主义所需的情感。这篇文章谴责不流血的 “开明” 左翼知识分子阶级没有理解这一点;他们是 “看到国旗时心从未跳动的人” ,而 “当时机到来时,他们会对革命退缩”。对奥威尔来说,重要的是国家在各地捍卫民主的情感力量。
奥威尔意识到了当前许多爱国主义复兴者所忘记的风险。爱国主义的呼吁就像知识分子生活中的鱼饵一样有效。鲨鱼会出来。我们这个时代的右翼想要拯救国家,愿意以国家的名义牺牲民主。凡是本土主义右翼崛起的地方,都有一批知识分子蜂拥而至,为国家出谋划策。印度的斯瓦潘·达斯古普塔、美国的乔纳·戈德堡和法国的埃里克·泽穆尔等人将金融家、人道主义者和校园 “活动家” 混为一谈,成为绝望的代言人,宣称要在即将到来的灭亡或国家复兴之间做出 “明确的选择”。他们冒充国家遗产的捍卫者。
曾经是左翼人士的法国哲学家阿兰·芬基尔克罗 (Alain Finkielkraut) 声称已经看到了曙光。他的反叛使他成为一个曾经崇尚西蒙娜·德·波伏瓦、阿尔伯特·加缪、和让·保罗·萨特的国家的媒体偶像。他的畅销书《不快乐的身份》(L’identité malheureuse)(2013年)警告说,由于穆斯林移民和布鲁塞尔灰色办公大楼里的欧洲官僚,法国正在衰落。芬基尔克罗关注的不仅仅是外来者;还有来自内部的褪色的爱国精神。像他在其他地方的同伴一样,他提出了可怕的预言,即 在未被同化的外国人和迷失方向的多元文化的本地人手中,法国将自取灭亡。
保守的民族主义也将其他人拉入了爱国主义复兴的事业中。在右翼民粹主义和全球精英的免税福利之间,进步人士也加入了这场争辩,并削弱了对国际主义的吸引力;全球化已成为一种耻辱的品牌。
吹嘘民族主义的美德,让全球理想主义者看到一个新的国家在追逐自己的事业。
巴拉克·奥巴马是美国世界性自我形象的代表,他体现了在从世界中撤退的同时振兴国家的困境。他的政治回忆录《应许之地》(A Promised Land,2020年)的圣经标题强调了一个主题,即 领导一个失去了领导意志的国家时的磨难。当奥巴马在2008年胜选时,他反思了杜波依斯(W E B DuBois)和美国黑人永远被谴责为双重身份:既是美国人又是黑人的概念。奥巴马向杜波依斯的才华鞠躬,“但我从未质疑过 — — 或让别人质疑 — — 我的基本 ‘美国性’”,他说。他的 “美国性” 的标志是对国家的特殊性的信仰,是自由和欢迎其他国家的模式。无论好坏,与之相联系的都是一个全球领导的传统,以反映其爱国主义的荣耀。
关于这本书,如果您错过了《应许之地的虚假承诺》
然而,奥巴马自己的外交政策是努力降低对美国在国外能做什么的期望,同时在国内鼓吹高大上。他写道,他对伊拉克战争的反对和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疑虑,都是基于 “对美国特殊性的信念,以及对我们按照自己的形象重塑世界的能力的谦逊”。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现实主义是如此令人困惑和值得嘲笑。奥巴马声称要回归罗纳德·里根的遗产,但却没有定义它的勇气。特朗普信条中的道德荒原掩盖了奥巴马对中东独裁者的虐待行为、大规模驱逐出境、以及在叙利亚公开划清界限 — — 然后又走开的沉默。
如果您错过了《两个时代,同一种政治毒品》
这种在国内崇高的理想主义和在国外缩小的现实主义的混合体,由于需要激发公民的爱国热情、同时需要为他人打消爱国热情,在最近一个关于民族主义解决全球气候危机的力量的 “案例” 中显示出来。
Anatol Lieven 是一名在华盛顿特区工作的英国记者,他的报道范围从巴基斯坦到波罗的海共和国,并跨越了智囊团、博客圈和学术界的维稳工业综合体。他认为,现在是让气候活动家抛弃他们的乌托邦式的团结的时候了,从特朗普和巴西的博索纳罗、从莫迪到俄罗斯的普京等 “真诚的” 民族主义者手中夺取国家,并看到牺牲只有在对国家的呼吁下才能发挥作用。
这不是奥威尔那种为了更广泛的事业而集结在旗帜下;正如 Lieven 在《气候变化与民族国家》(2020)中所说的,“在愚蠢的、短视的民族主义版本和聪明的、远视的民族主义之间”。国际主义在这里无影无踪。Lieven 考虑引用一个更温和的爱国主义呼吁,“一个不太有争议的术语”。但为什么要大惊小怪呢?吹嘘肌肉发达的民族主义的优点,让全球理想主义者看着一个追逐自己事业的新国家的尾光。
理想主义者也夺回了 “国家”。吉尔·莱波尔可能是美国最有名的历史学家,作为一个熟练的作家和学者,她用古怪的故事揭示了更广泛的真相,并以无以伦比的成功架起了常春藤联盟和精英自由派媒体之间的桥梁。莱波尔还加入了国家建设俱乐部。她想从民族中心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的忽视中夺回国家,特别是在教授中,他们让国家的概念发霉,因为他们把注意力转向更小和更大的事;她在《The Case for the Nation》(2019年)中写道,在走向全球的过程中,他们 “放弃了国家历史”。这使得国家被 ‘不那么严谨的人’ 抢走了。在莱波尔看来,进步人士抛弃了国家;而坏人夺取了它。现在是时候把它找回来了。
在《外交事务》和《纽约客》等杂志的版面上,以及在《这个美国》中,莱波尔希望让这个国家对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人士来说再次变得很酷。她所说的国家是开放的、好客的、多元的、公民的。它把不同的人结合在一起,给他们以庇护,而不管他们的分歧。莱波尔将奴隶制和种族排斥的错误纳入主叙事;它们为未完成的、追求自由的情节线提供了紧张和戏剧性。
对莱波尔来说,重振爱国主义叙事意味着擦亮例外主义的主张,即 美国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它与其他国家不同,是天生的自由主义者。从建国的那一刻起,莱波尔就把这个国家从咆哮的本土主义者手中 拯救出来,因为正是这个国家的自由派叙事让它变得与众不同。如果没有自由主义这个关键的形容词,美国看起来就和其他国家没什么区别了。让美国 “再次伟大” 的骚乱者可能会独自声称爱这个国家,但 “他们将是错误的”,她在《这个美国》的结尾感叹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唾弃了那些使美国与众不同的东西;他们的民族主义将吞噬自由主义和使国家伟大的美德。成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的方式是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分享莱波尔的建国叙事。
在国家的组成中,是通过排除一些其他人来创建共融的。
莱波尔没有说的是,她的自由主义只有在国家的保障下才能生存;这就是她希望国家的概念回归的原因。她希望她的读者和她的学生们能像特朗普的军团一样,对挥舞美国国旗感到自豪。挑战是回到国家的浪漫,恢复对内部人的自由的集体记忆,即使外部人从视野中退去。
或者,从叙事中被粉饰掉。
莱波尔看不到的是她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想象力的排他性特征。她承认,美国的民族主义过去和现在都很 “复杂”。她所称的复杂性始于十三殖民地,除了一些有远见的宪章,如《联邦条例》,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但是,国家的构成就是通过包括一些人而排斥另一些人来建立共同体的。殖民地,首先,意味着征服和殖民化。但在莱波尔的叙述中,原住民、墨西哥人、夏威夷人和波多黎各人都是影子。为了恢复 “生而自由” 的国家神话,将其从种族灭绝的本土主义者手中“拯救”出来,意味着将其他人排除在故事之外,直到他们成为 “移民”,在其他地方寻求非自由主义的庇护。
【注:十三殖民地是指大英帝国于1607年至1733年在北美洲大西洋沿岸建立的一系列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最终成为了美国独立时的组成部分,即后来的美利坚合众国。 法兰西斯·德瑞克爵士率领的英国探险船队又再次为英国宣称占领包括华盛顿州的太平洋西北地区。】
如果您错过了《从暴民政治到取消文化》
莱波尔会同意奥威尔的观点。正如她所说,打败非自由主义的唯一方法是 “呼吁国家目标和目的”。但是,奥威尔会同意莱波尔的观点吗?我不这么认为。奥威尔从来没有把捍卫体面和权利看作是停止于祖国边界的事。更重要的是,是什么阻止了国家的排他性和灭绝性的权力肆意妄为?是全球团结和竞争的流动组合,使民族国家受到牵制,被边沁的 “国际” 所支撑,国家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分离出去。
那些主张恢复爱国主义叙事的人,不仅仅是在从逮捕学生、肢解记者、和流放知识分子的恶棍手中夺回国家。他们也在承认失败。他们实际上是在宣布结束寻找将国家成员身份与更广泛秩序的归属问题相协调的叙事。
1951年,汉娜·阿伦特对新的叙述发出了呼吁。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告诉读者,“只有在新的政治原则中,在地球上的新法律中,其有效性这次必须涵盖整个人类”,才能约束国家最糟糕的习惯。
是的,这必须考虑到领土民族国家的现实情况。但这个新的原则不应该允许我们把 “过去好的东西,简单地称之为我们的遗产”。她那个时代的恐怖 — — 以及溺水的难民的景象或孤儿的声音 — — 也同样真实。她在序言中写道:“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想从现在的严酷中逃脱出来、去怀念仍然完好无损的过去,或者去期待一个更好未来的遗忘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为了人类的利益,阿伦特敦促读者把国家看成是一种必需品,它能够做出如此残酷的事,永远不可能被委托去做善事。在大屠杀和一个世纪的帝国暴力之后,退回到怀旧的舒适中的诱惑 — — 通过回归其遗产使任何国家 “再次伟大” — — 都回避了创造叙事的挑战,超越了属于一个国家或一个使国家成为可能的世界的错误选择。
爱国主义复兴者 — — 如果他们想改善他们的 “案例” — — 需要正视一个悖论,而且要更加复杂。世界需要国家做善事,比如减少碳排放,停止将无国籍的人视为非人。
为了做善事,国家必须是善的。但好国家存在的条件是其他好国家为彼此做善事 — — 以及为那些因为他们的国家很糟糕而失去家园的人做善事。在为新的全球时代寻求新的国家故事时,为什么不从这里开始呢?⚪️